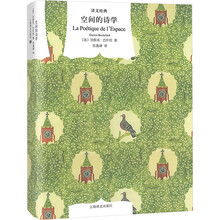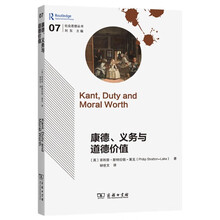《胡塞尔哲学中的意义问题研究》:
胡塞尔之前提到的符号的象征性用法和意指是不矛盾的,任何表述都能分出象征这个可能的矢量(如胡塞尔所言:“象征思维只是因为新的'意向'特征或行为特征的缘故才是一个思维,这个特征使有含义的符号与'单纯的'符号得以区分开来”),在无直观的表述行为那里,同样存在这种象征性的但仍然是理解性的特征(“象征”的这个特征和“指示”的特征是十分相近的)。由于象征、指示的随意性和偶缘性,所以“各种单纯象征的含义意向彼此之间常常没有清楚的区别”,这样就使得无法可靠地、容易地对其认同和区分,比如可以用蚊子象征大象(比如在游戏密码中),这在实践上是可行的,由此显然不能依据表述的象征性特征来区分蚊子和大象的含义,所以才需要借助于“直观”的手段,通过回溯蚊子大象的直观起源,就可以在理论上区分出蚊子和大象而排除实际中的偶然的各种象征性情况。胡塞尔此时还只是静态的在理论上为了排除象征的偶然性从而确定建立在含义中的真理,显然真理和直观相连契,这保持了胡塞尔对于真理的一贯看法。但这里胡塞尔诉诸直观、充实以最终区分含义,多少还带有和对表述的现象学分析无关的一种方法上的辅助作用[似乎只要我们把此语含义的区别(通过最终的回溯到的直观而)看作是既成的就行了];这里偶然性的情况和无直观的含义本身如何能够脱离直观而在实践中自由运用,此时的胡塞尔还未加以考虑,这留给后来的发生现象学来处理了。不过这一处处理的确可以看出胡塞尔持有一种在发生、起源上直观和充实的优先性立场,尽管表述就其本身的本质(含义意向)无关于直观(所以在《观念1》中他把表述作为一个单独的logos层,而其他的感性、直观的层次的行为都可以映射到这个层次上来。参见《胡塞尔哲学中的意义问题研究》第十章第二节)。以上这些考虑指明了第六研究的任务,即分析含义和认识之间、含义和澄清性直观之间的关系,讨论充实性意义从而完满地阐明含义问题[但那里仍没有考虑不带直观、充实地表述的自由行为]。从这种安排的体例上可以看出胡塞尔在含义问题上的确存在一个发生学领域,只是此时尚未成熟,不能完整地阐明含义问题,这并不意味着胡塞尔无法处理无直观的意向行为。
在直观和真理的关联上可以看出胡塞尔和康德的一致性:“康德把感性直观看作是我们全部认识和思维(知性)的基础、对象、内容、质料的唯一来源,他说:'一切思维不论是直截了当地(直接地)还是拐弯抹角的(间接地),都必须借助于某些标志最终与直观相关联。'”这里可以想到无论表述是否带有直观,它最终都可以回溯到直观上来,胡塞尔和康德的认识论都强调直观作为知识或思维的最终的外部来源。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