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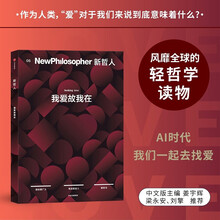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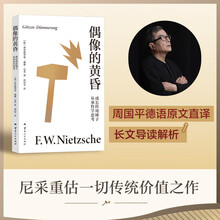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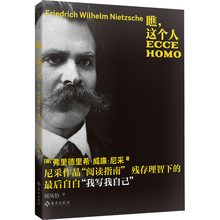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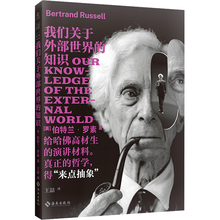

乔治·巴塔耶,博学多识的巨匠,后现代思想的策源地之一。苏珊·桑塔格称他为“爱欲与死亡的大师”,哈贝马斯认为他是尼采的继承者。《内在体验》集中展现了他哲学观点中很重要的一些概念,其观点振聋发聩,曾令萨特大为惊愕,著文批判。在《内在体验》中,巴塔耶的行文方式深受尼采及克尔凯郭尔影响,他以哲理名言、思考札记形式构建全书,用饱含激情的方式表达他对生命、死亡和内在体验的思考,妙笔生花,富于哲理。
此书为巴塔耶的重要代表作之一,为其“无神学大全”三部曲的第一部。该书出版于二战期间,是巴塔耶治疗肺病期间智力劳作的产物,他的主要哲学概念——耗费、逾越、祝祭、神圣情色,他有关生命、死亡与内在体验的沉思,均赖此书得以深刻展示。
VI
尼采
关于一场以万物为祭品的献祭
当我写作时,焦虑来临。记述(récit)一旦开始,便在我眼前,始终被涂改得一团黑,它渴求墨水。但对我而言,设想它已经足够。不得不完成它且不从中期待什么,这让我惶惑。
回忆着洛特雷阿蒙(Lautréamont)的《诗》(Poésies),[1]我设法颠倒主祷文(Pater)的用词。[2]我想象如下的对话,作为一个后续的故事:
我沉睡。纵然缄默,上帝对我述说,用低沉的声音,暗示影射,如在爱中:
——我在尘世的父,愿人尊你的恶为拯救。愿我诱你堕落。愿你辱骂我,如同我辱骂那些爱我的人。我苦涩的饮食,今日赐给我。免我在天国的意志,如同免了在尘世的意志。让我脱离无能。乏味无趣,全是我的。
犹豫着,烦恼着,我回应道:
——阿们。
人们在他的上帝面前最不诚实了:他不允许有罪过!
——《善恶的彼岸》,65a[3]
我靠上帝来否认他自己,厌恶他自己,把他敢做的,把他所是的,抛入缺席,抛入死亡。当我是上帝的时候,我否定他,直至否定的深处。如果我只是我自己,我就不知道上帝。只要清晰的认知在我身上持续,我就命名了他而不认识他:我不知道他。我试着认识他:很快,我就变成了非知,变成了上帝,未知的、不可认知的无知(ignorance inconnue, inconnaissable)。
宗教残忍是一架长梯,有许多梯级;其中有三个是最重要的。以前人们以人,也许恰恰是他们最爱的那个人为上帝的牺牲品,——属于此类的有一切史前宗教的童男童女牺牲,还有提庇留皇帝(罗马所有时代的错乱人物中最令人毛骨悚然的那一位)在卡普里岛的秘密洞穴里所献的牺牲。然后,在人类的道德时期,人们为他的上帝牺牲他们所秉有的最强健的本能,他的‘自然’;这种节日欢乐,就闪耀在苦修者、激动的‘反自然者’的残忍目光中。最后:还剩下什么可以牺牲的?人们最后莫非必须把一切慰藉者、神圣者、救治者,一切希望、对隐蔽的和谐、对未来的诸种福气与正义的一切信仰都一下牺牲掉?莫非人们必须牺牲上帝本身,并且出于对自身的残忍去祷拜石头、愚蠢、困难、命运和虚无?为了虚无牺牲上帝——最后一级残忍的这种悖谬的殉道,始终是留给那个现在即将到来的世系去做的:我们所有人都已经认识其中的一些了。
——《善恶的彼岸》,55[4]
我相信,一个人祭献他所滥用的财物(使用只是一种根本的滥用)。
人是贪婪的,他被迫如此,但他谴责贪婪,这只是他所忍受的必要性——他把其自身的赠礼(don),或他所占有之财物的赠礼,高高地举起,只有赠礼彰显了荣耀。他把动植物变成他的食物,但在动植物身上,他认识到了和他自身相似的神圣性,因此,一个人没法不加冒犯地摧毁它们,消耗它们。在人所吸收的每一个(有益于他的)元素面前,他感到自己有义务承认他对元素的滥用。其中的一些人负责辨认那成为祭品的植物或动物。这些人同植物或动物有着神圣的关系,他们不吃动植物,而是把动植物给另一群人吃。如果他们吃动植物,那也是通过一种富有启发的精打细算:他们已经提前认识到消耗的不合理的、严重的、悲剧的特点。人只能靠毁灭、杀戮、吸收而活着,这难道不是一个悲剧吗?
不仅是动植物,还有其他的人。
没有什么能够遏制人的前行。如果人成为了一切,那么,就只有饱足了(如果不是对每个人而言——绝大多数的个体必定抛弃了他们自己的需求——至少也是对整体而言)。
在这条道路上,一个人对其他人的奴役,是一步,但只是一步:他把他的同类变成了一个像动植物一样被占有和吸收的物。但人成为人之物的事实,产生了如是的反弹:奴隶变成了主人的物,而主人——他是至尊者(souverain)——从共融(communion)中撤出,粉碎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communication)。至尊者对共同法则的违背开启了人的孤立:人的分离(séparation)只有在最初那时候才能被勉强地重新统一起来,此后就绝不可能了。
主人对可被吃掉的囚徒或手无寸铁的奴隶的占有,把人自身,如同(不再不恰当地,而是和动植物一样)服从挪用(appropriation)的自然,置于那些必定要被不时地牺牲掉的对象当中。而且,人恰好遭受着生存与国王的分离所导致的交流之缺席。为了确保他们返回所有人的共融,他们不得不处死国王,而不是奴隶。所以,在人中间,看上去肯定选不出一个比国王更配挨刀子的人了。但对于军事领袖,献祭不再可能(一个战争的指挥官太过强大)。狂欢节上的国王(死前被喂饱了的、乔装打扮的囚犯)取代了他们。
牺牲了虚假国王的农神节,允许人们暂时地回归黄金时代。角色被颠倒了:主人侍奉了奴隶一次,而这样一个代表主人权力——这个权力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分裂——的人,随后就被处死,这确保了每个人在一场唯一的舞蹈(甚至在一种唯一的苦恼、在一阵快乐的唯一的迸发)当中,实现融合。
但人对一切可挪用之资源的挪用不只限于活生生的有机物。我说的不是近来对自然资源的无情开采(不是一种产业,虽然我常常惊讶于它的灾祸——失衡——几乎没有在它造就繁荣的同时得到察觉),而是人的心灵:全部的挪用为了人的利益而进行,但人的心灵——由此不同于只消化食物、而从不消化自身的胃——最终把它自身变成了一个物(一个被挪用的对象)。人的心灵已经成为了它自身的奴隶,并且,通过操作所假定的自家消化(autodigestion),它已经消耗、抑制、毁灭了自身。正如他所装配的齿轮内部的一颗齿轮,人的心灵把自身变成了一种滥用,并且,其后果逃避了他——以至于这种后果只是到了最后才出现,而人身上持留的没有一样不是有用的东西。包括上帝在内的一切都被还原为奴役。一种啮齿动物的工作最终把他切碎,给他指派了位置;然后,由于一切是变动的、被不停地修改的,它又剥夺了位置,揭示了缺席或无用。
如果一个人说“上帝死了”,那么,有人想到了耶稣,耶稣的牺牲,像国王的牺牲一样,带回了黄金时代(天上的王国)(然而,死去的只是耶稣,离弃耶稣的上帝无论如何在等待他,让他坐在自己的右边[5]);还有人想到了我刚刚提及的滥用,这种滥用不允许任何的价值存留——心灵,根据笛卡尔的公式,被还原为“有益人生的明白可靠的认知”。但“上帝应该死了”,成为一场献祭的牺牲品:这要有意义,就必须深刻,并且,就像一场把祭品神圣化的活人献祭不同于一种把祭品当作劳动工具的奴隶制一样,不同于上帝在一个清晰的、奴役的世界观念当中的遁避。
我日益明白一点,即从学术书籍中得出的观念——和图腾崇拜、献祭一样——参与了一种理智的奴役:如果我回想一个历史的事实,那么,在被挪用或被消化的事物的谈论中体现的滥用,就愈发地让我无能为力。并非错误的部分打击了我:那是不可避免的。而是由于我接受了犯错,我就更不害怕它。我谦卑,必定惴惴不安地唤醒一个死去已久的过去。不管活着的人拥有关于过去的怎样的知识,他们并不像他们认为的那样占有过去:如果他们认为自己持有了过去,过去就逃避了他们。我给了自己借口:当我建造我的理论时,我没有忘记,它通向了一个逃离的运动;我只能以这样的方式定位我们所义不容辞的献祭。
由于我们内部不断增长的理智形式的奴性,我们是时候完成一场比前人之所做更加深刻的献祭了。我们再也不必用祭品来补偿我们对动植物和人的滥用。把人自身还原为奴役的做法如今(而且从此长久地)在政治领域里自食其果(好事是废除滥用,而非得出宗教的结果)。但人后期对其理性的至高滥用要求一场最终的献祭:理性,可理解性,人所站的地面本身,必须遭到拒斥,在人身上,上帝必须死去,这就是恐惧的深处,是他所屈服的极限。只有一刻不停地逃离那紧紧抓住他的贪婪,人才能发现他自己。
[1] 参见洛特雷阿蒙:《马尔多罗之歌》,车槿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219-258页。——译注
[2] 主祷文见《马太福音》6:9-13:“所以,你们祷告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译注
[3] 尼采:《善恶的彼岸》,赵千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98页。——译注
[4] 尼采:《善恶的彼岸》,赵千帆译,第84-85页。——译注
[5] 参见《新约·使徒行传》7:56:“我看见天开了,人子站在神的右边。”或《使徒信经》第6行:“他(耶稣)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译注
……
内在体验
序 言
第一部分 内在体验导论草案
I. 教条奴役(与神秘主义)批判
II. 体验,唯一的权威,唯一的价值
III. 一个方法的原则和一个共通体的原则
第二部分 刑苦
第三部分 刑苦前记(或喜剧)
我要把我个人扛至尖顶
死亡在某种意义上是一场欺骗
天空之蓝
迷宫(或存在的构成)
“交流”
第四部分 刑苦后记(或新神秘神学)
I. 上帝
II. 笛卡尔
III. 黑格尔
IV. 迷狂
V. 时运
VI. 尼采
第五部分 给我满把的百合花吧
荣归我颂
上帝
沉思的方法
序 言
第一部分 质疑
第二部分 决断的立场
第三部分 裸体
1953年后记
注 释
乔治·巴塔耶和海德格尔是尼采重要的继承者,这两个人,是尼采通往法国后现代思想的两个必经之道。
——尤尔根·哈贝马斯
你如何对巴塔耶这样的作家进行分类·小说家、诗人、散文家、经济学家、哲学家,还是神秘主义者·答案如此之难,以至于文学手册总是忘掉了巴塔耶。
——罗兰·巴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