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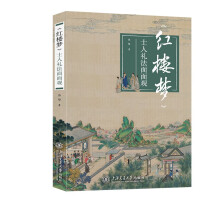
宗教、道德与法律的关系、社会中个人自由的限制、道德领域的公私界限以及法律的介入点,这是德富林勋爵在该书中讨论的若干核心问题。
关于同性恋问题的沃尔芬登报告主张存在一个位于法律之外的私德领域,德富林驳斥了这一相反论点。不论何种情况,争论取决于公私领域的定义,而在写作过程中,德富林勋爵考察了约翰·斯图亚特·密尔《论自由》中的教义,那是诸多论证的渊薮。
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世俗社会,所以就不再允许通过某一宗教信仰证成任何法律,尽管由于其命令与禁律的力量,道德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宗教。然而,德富林坚决主张,法律仍纯粹关乎共同道德事实,而非关乎法律应当如何的任何哲学或宗教观念。立法者应当弄清的不是正确信念,而是共同信念。那些服务于法律的人有责任保护“实然法律、实然道德、实然自由——它们并不完美,却保持其社会之既有而不至沦丧”。
辑于该书的七篇文章曾作为英国与美国的讲义发表于不同时间。然而它们都围绕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宗旨而相连,并详细考察道德律与刑法、准刑法、侵权法、合同法、婚姻法各部门法的关系。
译后记
法律与道德关系是法理学之枢轴。当代分析法学家哈特与富勒、德富林、德沃金的三大论战精彩纷呈,相关名著在中国学界已广为阅览、备受称道,富勒《法律的道德性》跻身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名著”,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法律帝国》位居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外国法律文库”,均早已荣登法科学人经典柜架。唯德富林《道德的法律强制》一书仍遥隔海外,无缘直睹堂奥,殊为学林憾事。
作为英国著名法学家、律师、大法官,德富林勋爵一贯主张法律可以强制执行道德。1957年沃尔芬登勋爵主持的《关于同性恋犯罪与卖淫的委员会报告》建议,成人之间合意的同性恋行为不再视为犯罪,并由此主张应有一个不受法律调整的私德领域。于是,德富林在1959年的演讲中以“道德的法律强制”为主题反对委员会的意见,旋即引致英国法学家哈特、美国法学家德沃金等学者的激烈批判。诚如《泰晤士报》所描绘,德富林与哈特等人的这场论战是一场“艰苦卓绝、激情荡漾、交相问难而富有价值的论战”,堪称20世纪法理学著名论战之一,并引发英美法学界的广泛评述。至今,这场论战仍不啻为思索道德与法律关系的理论渊薮,也是探讨社会道德、法律价值、自由主义、民主原则、家长主义、刑法功能、损害原则等重要论题之前应予重述检思的学史华章。
或许通过哈特《法律、自由与道德》(支振锋中译本)与德沃金《认真对待权利》(信春鹰、吴玉章中译本),也可一窥德富林勋爵所倡道德的法律强制之理论概貌。然而,该理论的现实缘由如此宣显,以致坚持同性恋是不道德行为以反对沃尔芬登委员会非罪化建议的具体观点,聚拢了学界的批判眼光与媒体的舆论反思。[1]若仅就德富林反对沃尔芬登委员会报告的意见陈陈相因,盖不免遮蔽辜负其道德与法律一般理论的价值。在对自由主义心驰神往、唯理性话语马首是瞻、朝分离命题趋之若鹜的思想氛围中,更易于否弃德富林道德法律强制理论的普遍意义,及其对民主、自由问题的有益思考。
尽管如此,起初涉猎批评者之见,进而浅尝该书宏旨,译者仍心有戚戚,豁然雾解,一方面是其社会道德言说与“损害”、“瓦解”之联结所形成的法律发展的洞识与法律功能的解释,另一方面是其颇受訾议的“厌恶”、“不能容忍”词汇所透露的、与法律精英话语、理性主义有所龃龉的公共信念、公共情感及民主立场。因而,尽管未必认同德富林对沃尔芬登委员会建议的批判,仍赞赏其道德法律强制理论对法律现象的解释力及在价值立场上的说服力。[2]遂萌发译介之念,累年方得偿夙愿。
一
德富林的核心观点也许难以一语归结,但这番论述无疑最为直观而激发争论:社会即观念共同体,如无缝之网,损害必不可少之公共道德将有可能导致共同体走向瓦解,如果承认公共道德对社会是必要的,就必须支持运用道德教化与法律强制维系公共道德。这正是哈特在《社会团结与道德的法律强制》一文所批判的核心论点,后来德沃金归纳为“瓦解命题”。社会道德与法律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作为一种普遍性的理论,“瓦解命题”富有社会规范理论的解释意义,一方面从根源上解释社会控制的发生及道德对法律形成、发展的作用,呈现出一种通过社会道德陈述法律功能的基本主张,另一方面阐明法律权威不能脱离道德基础,试图祛除或淡化法律中的共同道德因素,将不利于法律权威的树立与维持。
但哈特指出,涂尔干与德富林的理论总体相似,都主张只要在受到“强烈而清晰”(涂尔干)或“无法容忍、愤怒、厌恶”(德富林)的支持之处,道德法典就被强制执行,否则就会造成社会“成员相互疏离”(涂尔干)或社会“瓦解”(德富林)。提取“历史表明,道德联系的松弛往往是社会瓦解的第一步”为德富林的核心论述,哈特递进式地批判这一“瓦解命题”,可归纳为证据、社会之概念、程度、道德普遍性、因果、价值六方面的批判:
其一,证据问题:“瓦解命题”是一种经验化陈述,务必给出证据充分论证,而德富林未给出这类证据。从而,哈特认为需要的证据类型包括:共同道德恶性变化引致社会瓦解的历史证据(涉及“程度问题”)、维系共同道德方案的替代方式引致社会瓦解的心理学证据(涉及“价值问题”)。
其二,社会之概念问题:如果“瓦解命题”仅指涉观念共同体意义上的社会,那么“社会”当然可以改变、消亡、接替,但描述为“瓦解”或“成员相互疏离”则有危言耸听之嫌。
其三,程度问题:应当区分两种“瓦解”或“变化”:一种是社会道德自然或良性的变化或“容忍限度变迁”的正常现象,另一种是社会道德恶性形式变化,即反对社会受到保护并最终导致个人背离社会道德的结果。哈特认为,瓦解命题所需要的历史证据在于后者,即共同道德恶性变化引致社会瓦解,但旋即指出古今社会形态存在巨大差别,所以在程度问题上“历史证据”又往往不足为据;
其四,道德普遍性问题:社会道德可以分为普遍意义的最低限度道德与特殊意义的社会道德律。对普遍社会最低限度道德的法律强制可以成为共识,而特殊社会共同道德的法律强制,则不过是保守社会的外围工事。
其五,因果问题:不管“瓦解命题”陈述的共同道德是普遍意义的社会道德,还是特定社会的道德律,都无法主张共同道德之维系与防止瓦解或“相互疏离”之间的必然联系。言下之意,即便提供某些历史“证据”,仍不足以主张这种因果关系。
其六,价值问题:“瓦解命题”对因道德变化的社会“瓦解”证据诉诸替代社会类型的分析:如果呈现为自由放任类型,不能经由道德作为“无缝之网”的逻辑,将之夸大为社会约束的总体失效,相反,这有可能增进自由生活及对暴力的约束;如果呈现为道德多元类型,则现代生活完全可以容纳道德分歧,且多元道德比单一道德更富吸引力。
后来的评述者(如阿尼森教授)多认为,哈特以精湛的社会概念辨析揭示德富林含糊的社会观,从而成功驳倒其“瓦解命题”。德沃金也提到,反对者认为这种“社会瓦解”是天方夜谭,只有社会威胁迫在眉睫时才可证成道德的法律强制。其实,在肆意指责德富林“社会”概念含混不清、“社会瓦解”命题危言耸听之前,仍应考察德富林的相关回应:
其一,在“社会之概念问题”上应认真对待德富林第一讲长脚注的回应。哈特举“英国社会”的语义旨在说明,按德富林的社会概念则“封建英国社会”与“当代英国社会”是两个社会,但日常概念用法很可能会表述为一个延续的英国社会。可不管我们对社会实质变化的理解如何,诸如“旧社会”、“新社会”语词恐怕也在吻合“社会瓦解”命题的意义上使用,背后也透露出某种社会道德明显变迁的感知。[3]而且,德富林以“规则”与“游戏”、“条款”与“合同”的精当比喻,生动说明道德与社会的关系,在其“事关言辞”的理解上这番辩解言简意赅。
其二,在“程度问题”上不妨考虑德富林各处讲义对大部分人从事不道德行为之社会危害(有形的与无形的)的扼要陈述。这是德富林之所以提出与道德强制执行相关的立法权不存在理论限制的基础。德富林屡屡提及可能或事实上对醉酒、赌博、吸毒、卖淫、通奸、同性恋等行为进行立法控制的经典例子[4],有观于现实立法例的法学家不易辩驳。虽然德富林确未就同性恋之社会威胁的证据谈论更多,但批评者也不可能否认其社会大部分人同性恋的社会威胁,所以批判的重心往往就不是道德法律强制的理论命题,而只是现实状况下同性恋入罪的实践观点。那么问题就在于“程度”,设想“社会瓦解”的关键不就在于“超出部分”吗?只有过量才意味社会威胁,那么立法权的限制点难道不正是导致危险的过量部分?这一颇难应对的质疑,其实属于实践权衡而非德富林所说的“理论限制”。德富林一方面始终坚持不道德行为的法律限制是原则问题,法律实践操作是权衡问题,另一方面则重申无法划分不道德行为安全界限故应从严的态度。总之,存在不道德行为对社会有严重影响,从而引起政策与法律的干预以免社会恶化,观诸古今各式社会体系,恐怕难以否认这一事实。
其三,至于道德变化对社会与法律的影响这一“因果问题”,哈特认为德富林过于突出道德的整体性。哈特冠之以“无缝之网”,德富林反而认为这正是对社会影响的有力比喻,坚持认为道德就是一张信念之网,而非一些毫不相干的信念而已,从而阐明道德的局部改变会带来全局影响。在理解阐释道德信念的意义上,究竟是道德信念存在广泛的普遍联系,牵一发而动全身,还是说能够剖分道德领域(如公私问题)、厘定道德影响程度,也许见仁见智。可是在共同道德与社会维系的因果问题上,又回到社会之概念问题了。例如,德富林当然认为一夫一妻制变成多偶制就是“社会瓦解”,而哈特则不以为然。
分析法学关于法律与道德关系的分离命题,乍看起来并未明显呈现于哈特与德富林数回合的交锋中。回顾哈特该文的观点,主要是批判涂尔干、德富林“社会”概念的模糊与“社会瓦解”论的证据缺乏,似乎并未以道德法律分离命题为中心立论。但另外的批判观点要从《法律、自由与道德》一书中获致。原来,哈特是基于密尔自由主义“损害原则”间接处理道德与法律关系问题。这是一种倡导尊重个人思想与行动自由,通过特定“损害”考量法律强制正当性,而往往易于从实践角度“分离”法律与道德的原则。
若要正视道德在法律发展中的意义,或承认涉及道德法律强制之实在法的合理性,就无法以密尔自由教义及损害原则作实践解释。正如密尔的追随者莫利干脆以“应然”与“实然”(尽管这里的“实然”在对方看来也涉及“应然”)之别澄明,密尔主义法律观与斯蒂芬历史文化进路的法律解释风马牛不相及。若否认道德强制执行构成法律发展与实在法的一种合理解释,那就需要另一番实践解释。这也是哈特之所以提供一种密尔教义修正版的缘由。可在德富林看来,哈特的修正版是对密尔自由主义的一种阉割,不免讥讽“航行于密尔自由旗帜下的一些船员,竟会叛变并将家长主义旗帜升上桅杆”。依循德富林的理解,家长主义正应当让所有道德成为法律的事务,那种似乎旨在声称物质家长主义的解释,根本不可能与道德家长主义判然分离,从而实质上仍不免延展为完全的家长主义。而如果区别在于道德强制主义(运用法律强制道德)与完全的家长主义(运用法律强迫某人为自身道德良善的行事),则更是无法成立,因为如果社会与法律强迫一个人为自身道德良善行事,那就是在强制执行道德律。
[1] 诚然,基督教传统视同性恋为罪,德富林作为虔诚教徒有卫教本能,哈特作为同性恋者有某种情感紧张,也是解读论战所必要的“知人论世”。
[2] 此番译稿,读到秉持家长主义的学者杰拉德·德沃金《德富林是对的:法律与道德强制执行》一文时,对其开宗明义之态度深以为然:在涉及同性恋是否应当刑事化的具体立场观点上,他站在哈特一边;而对证成刑事化的损害行为与不道德行为之间的一般理论问题,他站在德富林一边。
[3] 正如梁治平先生曾以“道德与法律之争:清末社会崩溃的征兆”为题(该文亦略及德富林的观点),阐释礼教松弛与清末社会共同体与文化共同体的瓦解。
[4] 读到这些例证,不禁联想到清末礼法之争时,劳乃宣就“无夫奸”非罪问题反驳沈家本,举出“鸦片烟之罪”、“赌博之罪”的驳例,以说明可用刑法调整不道德行为,而不管实际上是否完全有效。
第一讲 道德与刑法 /
第二讲 道德与准刑法及侵权法 /
第三讲 道德与合同法 /
第四讲 道德与婚姻法 /
第五讲 民主与道德 /
第六讲 密尔论道德中的自由 /
第七讲 道德与当代社会现实 /
附录:
赫伯特·哈特:社会团结与道德的法律强制 /
罗纳德·德沃金:德富林勋爵及道德的法律强制 /
理查德·阿尼森:再论道德的法律强制 /
译后记 /
斯蒂芬与德富林不仅极好地提出诸多具体的例证,还以法律从业者熟稔老练的刑法运转经验阐发其深思熟虑之见解。其凝思仍广为英美国家之法律人所秉持,甚至比密尔之自由学说还要更为流行。——赫伯特?哈特
德富林的演讲引发一股反驳的潮流,从学术性杂志迅速溢出而席卷广播和完全大众化的传播媒介。……美国法学家应关注德富林勋爵的论证。虽然精读之后可消除某些批评家所发现的言过其实的迟钝,但是德富林的结论仍不会受欢迎。无论受欢迎与否,只要我们确信可以接触到,就无权忽视他的论证。——罗纳德?德沃金
每番阐述均才华横溢、洞明练达且独出心裁。——芭芭拉?伍顿
这是场艰苦卓绝、激情荡漾、交相问难而富有价值的论战。——《泰晤士报》
阅读每讲都是愉悦之旅,它们生动、雅致且与众不同。——《卫报》
这些文章源自有影响力且见识深刻的法学家之一,构成对我们时代至关重要问题之一的宝贵贡献,并呈现出我们所能从德富林勋爵那儿期待的富有透彻性与说服力的阐释。——《律师杂志》
自斯蒂芬法官先生批判密尔《论自由》及其信徒莫利的回应以来,德富林勋爵开启了对刑法与道德关系意义深远的重审,故而我们都如沐春风。——《新黑衣修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