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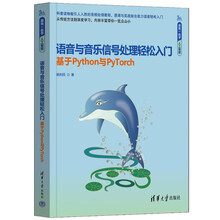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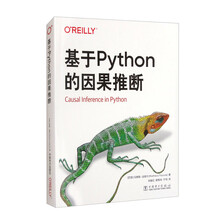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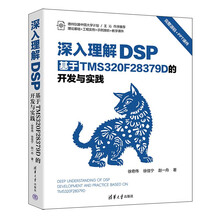
《科学源流译丛:无限与视角》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向关心科学和哲学的人揭示了近代早期科学、艺术与哲学的关系,告诉人们近代科学与哲学如何发端于同一个更深刻的根源。哈里斯通过详细解读中世纪哲学家库萨的尼古拉、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阿尔贝蒂、哥白尼、亚里士多德、笛卡尔、伽利略和现代哲学家布鲁门贝格,研究了这一主题。他的结论是,人性最大的愿望就认识,人的本性一次次地要求他超出由他在世界上的地位所赋予他的视角,从而肯定了自由,拒斥了虚无主义。
中译本序
我在本书第十六章提到,海森伯在《当代物理学的自然图景》(Das Naturbild der heutigen Physik)中引用庄子的一则故事来表达他的担忧:我们的技术已经不再是一种帮助我们活得更加人性的工具,而是可能剥夺人性,成为第二种本性。2007年,我在上海复旦大学作系列讲座时又一次想到了这个故事。在我看来,与技术和地球达成一种真正恰当的关系,实在太过重要。多年来,这些关切一直萦绕在我心中,这正是我撰写《无限与视角》的动机。该书考察了我们现代世界的起源,以更好地理解我们对实在的理解(这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前提)的正当性和局限性。我的关切正如庄子在2500多年前那则故事中所说:
子贡南游于楚,反于晋,过汉阴,见一丈人方将为圃畦,凿隧而入井,抱瓮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见功寡。子贡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夫子不欲乎?”为圃者仰而视之曰:“奈何?”曰:“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机心存于胸中则纯白不备。纯白不备则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载也。吾非不知,羞而不为也。”子贡瞒然惭,俯而不对。
在海森伯看来,这则故事在今天仍有重大意义。他指出,精神的不安“也许是在目前的危机中对人类状态的一种恰如其分的描述”。这种不安的根源在于一种持续改变世界的进步精神。不断进步的技术开辟了无数超乎想象的可能性,但同时也可能使我们疏离自身。自由的增长使一个问题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迫:什么能够约束这种自由?什么能够应对我们的不安?
当然,这是一则十分古老的故事,反映了一种非常不同的生活方式。技术和机器在世界各地的蔓延程度已经远远超出了中国圣贤的想象。但海森伯说的难道不对吗?我们难道不是必须学会让中国圣贤的智慧与机器共存吗?诚然,如果我们今天效法庄子笔下的为圃者,那将是完全不负责任的:无数问题要求我们接受他要我们拒绝的东西。拒绝技术就是拒绝面对我们今天的问题。我们需要更多、更好的技术。我们必须负责任地使用技术,这是毋庸置疑的。
然而,应当如何理解这种责任?海森伯认为,认真吸取这则故事的教益非常重要。关于现代世界图景的前提以及现代世界图景是如何由科学技术塑造的,我们理解得越深入,那位为圃者的忧虑就越显得有道理。今天的世界使我们不可能没有“机事”。为圃者说的不错:“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本书正是源于这样的忧虑,它试图帮助阐明现代世界的谱系,以更好地理解其正当性和局限性。
这一谱系的关键在于我所谓的“视角原理”(principle of perspective)。它可以很一般地表述如下:要把一个视角作为一个视角来思考,在某种意义上就已经超越了它,就已经认识到了它的局限。我们只能看到无法如其本身地显示自己的某种东西的一种视角性显现。要想意识到视角,不仅要意识到所看到的东西,而且要意识到我们特定的视角是如何让所看到的东西以那种方式显现的。
意识到我的视角如何让事物那样显现给我,不能脱离另一种认识:对某一特定视角的意识必然伴随着对其他可能视角的意识。这种意识是一种解放。当我认识到此时此地对我之所见施加的限制时,我必定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这些限制,能够想象和构想彼时彼地。我现在碰巧所处的位置并非牢狱。我不仅能够移动,而且在想象和思想中,我即使没有移动也能超越这些限制。自我能把自身提升到超越于最初束缚它的各种视角,这种能力要求作出越来越恰当的(即较少受视角束缚的)、在理想状况下真正客观的描述,从而要求一种越来越摆脱视角性扭曲的对实在的理解。正如本书试图表明的,科学的进步回应了这一要求。追求真理要求自由,而自由不承认任何限制。自由的理智使我们认为,甚至理性也对我们的见解构成了束缚。正如库萨的尼古拉、布鲁诺和笛卡儿所认识到的,我们的自由不可避免会把我们引向理性所无法把握的无限。庄子的为圃者所谴责的不安与我们的自由密不可分。作为本质上自由的存在者,我们只能梦想在天堂中获得安宁。
弗朗西斯·培根和笛卡儿等现代世界的创始人梦想有一种科学和技术能够创建这样一个天堂。这一梦想至今仍然很有活力,但它对理性要求太高,只可能是一个白日梦。尼采宣布上帝死了之后,人们意识到单凭理性无法提供真正的居所。我们内心深处对我们的客观化理性所提供的精神环境和物质环境感到不满。我们还想要某种不同的东西。但我们想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是两栖动物,既属于大地,又属于自由精神。于是,我们一方面试图亲近大地,梦想着庇护所和天堂;另一方面又要求自由,梦想着探索未知。我们还梦想有一种生存方式能够弥合归家的渴望与探索太空的向往之间的裂隙。但只有保持这一裂隙(它把我们沿着相反的方向拉扯),一种真正人性的栖居才有可能。
作为科学进步的代价,料想的中心和根基的不断丧失是否意味着人类不应试图使自己成为中心?人难道不是万物的量度吗?15世纪上半叶,阿尔贝蒂和库萨的尼古拉重新发现了普罗泰戈拉这一名言的重大意义,标志着现代世界图景开始出现,没过多久,该图景便会否认地球在宇宙中的中心位置。正如现代世界图景的开端所暗示的,地心说与人类中心主义之间并无逻辑关联,这也意味着,科学上宇宙中心的必然丧失与生存论上人类中心的丧失之间并无逻辑关联。毫无疑问,哥白尼革命以及后续革命否认我们的位置近乎于某个料想的宇宙中心。我这里不仅想到了康德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它否认我们能够认识事物本身;而且想到了达尔文革命,它要求把人理解成按照猿的形象而非神的形象创造的;我还想到了弗洛伊德革命,它要我们把自我理解成受制于无意识的冲动,这些冲动使我们无法做自己的主人。在某种意义上,科学的进步已经把人类远远抛在后面,抛得是如此之远,以致科学尽管致力于客观性,却不再能够看到完整的人,看到自由的、负责任的人。我们的生活世界虽然日益为技术所塑造,但并不能按照海德格尔所设想的技术世界图景,被客观化的理性所充分理解。海德格尔的《世界图景的时代》(Die Zeit des Weltbildes)一文虽然把握了某种本质,但仍然只是一幅漫画。科学技术尽管把我们远远抛在后面,但把我们留在了家里,给我们留下了家。
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天文学和宇宙航行学的进步,的确已经使世界祛魅。维特鲁威笔下的原始人仰望星空时,体验到那里有一种更高的、无时间的逻各斯。人类的居所曾在这种超越的逻各斯中找到了自己的量度。中世纪的人对星空的体验与此大体相同。但星空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人造光和空气污染已经使我们越来越难看到群星。把黑夜变成白昼的人造光、电脑屏幕的光不是已经足够亮了吗?我们的理性之光,这一“自然之光”(lumen naturale)不也是一样吗?科学使我们认为它与其说是一种天赋,不如说它本身就是自然的产物。哪里还需要神的存在?
然而,在地心说世界图景终结之后,在上帝死了之后,仍然有一种需求留存了下来:不在宇宙中感到孤独,希望体验到某种精神能对我们自己的精神作出回应。我们的科学难道不是要求有地外智能生命存在吗?现代世界图景让我们把地球看成绝不是独一无二的,与此同样古老的是相信我们迟早会在某处遇到智能生命。库萨的尼古拉从古代和中世纪家园般的宇宙中剥夺了地球的中心位置,并用一个无限宇宙取而代之。他已经设想其他星球上可能存在着智慧居民,这种想法将在布鲁诺、开普勒乃至开明的康德那里一再重现。尽管这些期待一再受挫,尽管目前的细节仍然模糊不清,但我们的科学依然试图证明这些期待是正当的,因为它坚称智能生命是自然过程的产物。物质从一开始就必定会产生精神。考虑到我们的准无限宇宙,认为智能生命只出现过一次,也就是在这个地球上,这难道不是另一种人类中心主义偏见吗?科学不会为真正独一无二的东西留出余地。科学所能理解的一切都是原则上可重复的。
不幸的是,除地球以外,事实证明我们的行星系非常不适合居住。虽然在月亮和火星上据说已经发现了冰的遗迹,但并未发现智能生命的遗迹。我们的天文学家用望远镜探入了更远的太空,也就是更远地追溯宇宙的历史,但并未发现我们所希望或畏惧的地外生命。天文学每进展一步,我们就越确信自己是孤独的。汉斯·布鲁门伯格(我追随他思考这些问题,并把本书献给他)把自己视为被技术留在家里的人。他促请我们也把自己视为被科学、技术和宇宙航行学的进步留在家里的人。留在家里!这可能意味着没有充分享用精神的发展及其承诺,但也可能意味着,进步为我们留下了我们的家,没有摧毁我们人类将永远拥有的这个唯一的家。虽然我们的理性已经把地球移出了宇宙的中心,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把地球体验为我们生活的中心。把一个人当作一个人来体验是体验某种独特的东西,把一朵美丽的花当作这朵花来体验也是如此。客观化的理性无法公正对待这种体验。我们必须牢记这种局限性。
伊卡洛斯受太阳光芒的引诱,在地球上方展翅高飞,最终却坠落海洋。我们这些随同布鲁门伯格把自己视为被技术进步留在家里的人,不会受这种伊卡洛斯式飞翔前景的诱惑,尽管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们可以安详地坐在房间里,饶有兴致地读着各种勇敢探险家的经历,即使他们的飞翔有时会以灾难而告终。我们知道,追求真理需要这样的飞翔。但我们也了解到,单凭理性不足以为生活赋予意义,那需要与他人一起居住在这个独特的地球上。因此,我们不会受太空探索的诱惑,设想有朝一日能够离开地球,在火星或其他某个天体上找到殖民地。恰恰相反!对这些旅行的思考只会使地球变得更加可爱和像家,一如冬季屋外肆虐的暴风雪会使我们更加感怀屋内的温暖。
只有在一种熟悉的精神显示自身的地方,我们才能体验到家的感觉。精神必须回应精神。因此,维特鲁威笔下的原始人才会以他们所理解的星空中的精神秩序为形象来建造房屋,它所庇护的是灵魂而非身体。但这种叙述在多大程度上对我们还有意义?今天还有谁在仰望星空时还能体验到一种更高的逻各斯的存在?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天文学的进步所带来的祛魅无法撤销。但这种祛魅正开始让位于一种越来越深的、日益增长的对我们脆弱地球的独特性的认识。不论是否喜欢,我们人类仍然与这个家园紧密联系着,它仍是我们生活世界的中心。我们出于自身的本性而与这个地球、与人类栖居的大地联系在一起,所有意义的根源都在其中。由这种洞见应当产生一种新的责任,它源于同时洞察到客观化理性的正当性和局限性。我们应当带着这种责任而在这个脆弱的地球上生活。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地心说。通过探究现代世界图景的根基,本书在结尾处作出了这一呼吁,当今的中国对此应有特殊的共鸣。
卡斯滕·哈里斯
2013年10月
前言
第一章 导言:现代的问题
第一部分:视角的力量与贫乏
第二章 视角和宇宙的无限
第三章 有学识的无知
第四章 阿尔贝蒂与透视建构
第五章 奇特的透视
第六章 阿里阿德涅之线
第二部分:无限与真理
第七章 真理作为上帝的所有物
第八章 空间的无限与人的无限
第九章 人的无限与上帝的无限
第十章 工匠人:重新发现普罗泰戈拉
第十一章 人的尊严
第三部分:地球的丧失
第十二章 哥白尼的人类中心主义
第十三章 布鲁诺的罪行
第十四章 伽利略的洞见与盲目
第十五章 无限的暗礁
第十六章 哥白尼革命
第十七章 尾声:宇宙航行学和宇宙心智学
索引
译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