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世界漫游记》:
第〇章 数字之前
走进皮埃尔皮克巴黎狭窄的公寓,我怔住了,臭气熏天的驱蚊器,让我受不了。皮克刚刚从亚马逊热带雨林回来,在那里,他和印第安部落的朋友相处了五个月之久。现在,他正在给带回来的礼物消毒。书房的墙上,随处可见远古的部落面具、长毛头饰 和花边竹篮。书架上堆满了专业学术的书籍。窗台上放着一个还没有解开的魔方。
我问,皮克,旅行如何?
“艰难。”他回答道。
皮克是一个语言学家。可能正是因为这一点,他说话时总是慢条斯理,过度咬文嚼字。虽然,他已经五十多岁,看上去还是很孩子气,他有一双明亮的蓝色眼睛,面色红润,有着一头柔软却凌乱的银发。他声音低沉,态度很热情。
师从美国杰出语言学家乔姆斯基,皮克现在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工作。近十年来,他一直潜心研究蒙杜鲁库人。蒙杜鲁库人是南美洲印第安人的一支,一共约七千人,他们生活在亚马逊河流域,在巴西境内。他们所聚居的地方是雨林地区,面积为威尔士国土面积的两倍。蒙杜鲁库人聚居在绵延的小村落里,依靠狩猎和采集生活。皮克对蒙杜鲁库人的语言特别感兴趣。蒙杜鲁库人的语言没有时态,没有复数名词,也没有超过“5”的数字。为了实地考察,皮克开始了一段旅程,堪称一次伟大的探险。距离印第安部落最近的机场在500英里外的圣塔伦。从那里沿塔巴赫斯河航行15小时,大约200英里,才能到达蒙杜鲁库。这里是曾经让淘金者疯狂的小镇,也是皮克旅程的最后补给站。上一次,他在蒙杜鲁库租了一辆吉普车,带上必备的电脑、太阳能板、电池、书籍,还有120加仑汽油,沿着横贯亚马逊的高速路行驶。这条公路是七十年代修筑的国道,非常华而不实,现在已经十分衰败,变成了一条不好走的泥泞小道。
皮克此行的目的地是杰可瑞卡加,那里距蒙杜鲁库有200多英里。我问他,开车去那要多久。“说不准,”皮克耸耸肩,说道,“可能要一辈子,也可能只要两三天。”
“那这次呢?”我追问道。
“你知道,你永远无法了解具体的时间,因为每次都不一样。如果一切顺利……在雨季,应该差不多十到十二小时吧。”
杰可瑞卡加位于蒙杜鲁库人群居区域的边缘地带。皮克在那等待印第安人,和他们协商是否可以用独木舟载他进入蒙杜鲁库人的领地。
我十分好奇,又询问道:“你等了多久?”
“我等了挺久的。不过还是一样,别问我具体多久。”
“所以你花了好几天时间?”我试探地询问道。
他皱了皱眉,迟疑片刻说道:“大概,两个星期吧”
离开巴黎一个多月后,皮克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当然,我也很想知道,从杰可瑞卡加到那些印第安人的村落具体需要花费多少时间。
不过,皮克现在显然对我查户口式的提问很不耐烦,“我说过了,说不准!”
我执著的问:“那这次呢?”
他吞吞吐吐的回答:“我不知道呀。我想……可能……两天……一天一夜……”
我越是追问皮克具体的数字,他越是不情愿告诉我。我开始激动起来,不明白他极不情愿的态度是否潜藏着法国人特有的不妥协精神,或者可以说是一种学术的严谨性,要不只是一般的逆反心理。我不再询问,我们开始说点别的。几个小时之后,我们都谈到了一种感觉,那就像待在一个不明之地很长时间,突然回到家一样,忽然,皮克打开了话匣子:“当我从亚马逊回来的时候,我好像没有时间和数字的概念,甚至没有空间的感觉。”他说,回来之后他经常忘记各种约定,还会被简单的方向问题搞得晕头转向。“我很难再适应巴黎的生活了,城市中有各种转角和直线,都让我难以适应。”皮克的叙述中没有任何定量的数据,他所产生的困扰一部分来自不同文化的冲击。在原始部落中,他长期和一些不能数数的人待在一起,使得他已经不能用数字来思考大千世界的万物。
虽然没有人知道确切的答案,但是,数字的存在不超过一万年的时间。这里,我所说的数字是关于数字的术语和符号。
算术又变得流行起来。三十年前,第一个廉价电子计算器的突然诞生,葬送了广泛运用的心算技巧,心算的倒退愈演愈烈。报纸上每日数学难题、带有算术难题的流行计算机游戏,使人们的头脑变得更敏锐,而且(在更高层次上)快速计算国际锦标赛每年都有。由德国计算机科学家拉夫?劳在2004年创立了心算世界杯,每两年举办一次。无疑,拉夫?劳的两大爱好:心算和收集特别的世界纪录(比如,在一分钟之内,将葡萄扔到15英尺远,并用嘴接住的世界记录,世界记录是55个)。英特网帮助他认识了很多拥有相同爱好的人——一般,心算者们都不是很外向。在世界范围内,计算者或“数学参赛选手”从世界各地来到莱比锡,有不少选手来自秘鲁、伊朗、阿尔及利亚或澳大利亚。
你如何评判计算能力?拉夫?劳采用吉尼斯世界记录的分类法——将两个8位数相乘,两个10位数相加,将六位数的平方根提取成8个数字,找到1600和2100年份之间任何一周的某一天。最后一项被称作日期计算,好像倒回到快速计算的黄金时期。当时,参赛者会问在场的一名观众生日日期,参赛者将立即说出日期是星期几。
参赛规则是比赛的灵魂所在,可能因为复杂的参赛规则,比赛失掉不少戏剧效果。最年幼的世界杯参赛者是一名来自印度的11岁男孩,他表演了“空气算盘”——他的双手在想象的算盘上快速地拨弄着,保持绝对安静,他时不时地写下计算结果。(比赛结果规定,只能写下最终结果。)8分钟25秒之后,西班牙人克多挥舞着手臂,就像一个兴奋的孩童。38岁的克多在短短的时间里,已经算完了10道两个8位数相乘的题目,他破了世界记录。这个成绩的确令人叹为观止,看着他就像担任监考工作人员一样令人兴奋。
然而,在所有缺席莱比锡世界杯的参赛者中,最著名的一位要数法国学生阿列克西?勒梅尔,他更希望用别的标准衡量自己的计算能力。2007年,勒梅尔27岁的时候,在伦敦科学博物馆得到了国际瞩目,他只用了70.2秒计算出13次平方根:
85,877,066,894,718,045,602,549,144,850,158,599,202,771,247,
748,960,878,023,151,390,314,284,284,465,842,798,373,290,
242,826,571,823,153,045,030,300,932,591,615,405,929,429,773,
640,895,967,991,430,381,763,526,613,357,308,674,592,650,724,
521,841,103,664,923,661,204,223
毫无疑问,勒梅尔的成绩更加令人惊叹。有200位的数字,可能用70.2秒都不能完全念完所有数字。那么,是否正如他所声称的一样,他就是前所未有的最了不起的快速计算者了呢?这在计算界是一个备受争议的事,回想200年前,科尔伯恩和乔治?彼得间的对局,在他们各自擅长的领域表现的很出色。
“13次平方为a”指的是,一个数字与自己相乘13次后,得到a。只有部分数字自乘13次后,能够得到200位数字。(答案是一个数目巨大的定数,在400兆左右,都是16位的数字,以2开头。)因为,13是个重要的数字,同时也被认为是个不吉利的数字,勒梅尔的计算法带有神秘气息。事实上,数字13确有它独特的优势。比如,2被连续相乘13次后,答案结尾仍然为2。数字3被连续相乘13次后,答案结尾还是3。这个规律同样适用于数字4、5、6、7、8、9。换句话说,任何数连续相乘13次后,答案的尾数都是原来数。那么,我们就轻易得到答案的尾数了,根本不需要任何计算。
勒梅尔有其一套算法,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可以用于14个数字相乘的计算。纯粹主义者们也许会说,他的技巧不是计算的天赋,更像是记住一长串数字的方法。他们还指出,勒梅尔不可能立即算出任何200位数字的13次根。在伦敦科学博物馆,给他几百个数字,让他随意选择一个计算。
勒梅尔的表现可以和过去传统舞台速算者的表现媲美。观众只能惊呼“哇!”,而来不及去理解计算过程。相反的,在心算世界杯上,克多面对乘法运算29513736×92842033时,没有任何别的方法或隐藏技巧,他只是使用简单的1到9的乘法表。计算两个8位数相乘的最快方法是使用印度经文规则“垂直和横向”,将原来运算破解成64个个位数乘法运算。结果,他平均只用不到51秒就得到正确答案。知道了他是如何解答这道题之后,好像看上去也没有那么难,尽管64道个位数乘法运算的确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我和莱比锡的参赛选手们聊天,发现他们中很多人因为维姆?克莱因而迷上了速算,克莱因是一位荷兰速算者,在1970年代很有名气。克莱因曾在马戏团和音乐厅工作多年,在1958年,他被欧洲顶尖的物理学会聘请,在日内瓦的欧洲粒子物理研究所工作,为物理学家们作复杂的快速计算。或许,他是最后一位受聘的人类快速计算者。随后,计算机的发展使得他的天赋变得不那么重要。他从研究所退休后,又回到演艺圈,经常出现在电视节目中。(实际上,克莱因是推行13次根计算法的第一人。)
在克莱因之前的一个世纪,有一个速算者名叫达瑟,同样受聘于一家科学研究机构,帮助他们速算。达瑟出生在德国汉堡,在他青少年时代就开始速算表演,他受到当时两位杰出的数学家的照顾。早在电子和机械计算出现之前,科学家们一直以来使用对数表解决复杂的乘除法运算。之后,我会详细解释,每个数字都有对数,需要经过计算分数相加的艰难过程。达瑟计算了前1005000个数字的自然对数,每个数字保留7位小数,他花了3年时间,完成整个工作,他说他很享受这项工作。之后,在数学家高斯的推荐下,达瑟又开始另一项艰巨的任务:编辑从7000000到10000000之间的所有数字的因子表。也就是说,他把每个数字看作有一定范围,计算它的因子,即用任何数分解这个数字。比如,7877433有两个因子:3和2625811。当达瑟37岁去世时,他完成了相当大的一部分运算。
除了以上这些艰巨的计算任务之外,还有一项计算让达瑟名垂千史,当达瑟还是孩子的时候,他就将圆周率计算到200位之多,在当时可以算最高纪录。
在自然界中,“圆”无处不在——你可以看到圆圆的满月,人类和动物的眼睛的瞳孔也是圆的,一只鸡蛋的横截面也是圆的。将一只狗拴在一根木棍上,狗拉紧绳子绕着木棍溜达时,也是绕出一个圆。圆是最简单的二维几何形状。当一个埃及农民计算在一个圆形田地里可以种多少稻谷时,或者当一个罗马技工估测多长的木头做成车轮时,他们都必须计算“圆”的问题。
古人们早已认识到,无论你画多大的圆,圆周和直径的比率总是一定的。(圆周是围绕圆的周长,直径是穿过圆的最长直线。)圆周率被称作PI,或者π,它的大小略大于3。所以,如果你将一个圆的直径取出,围绕这个圆的圆周,你将发现,周长大概是直径的3倍多一点。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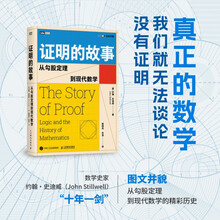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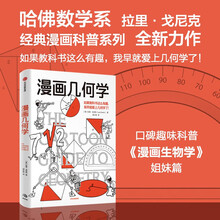


——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