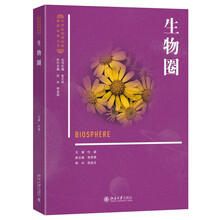第一章 从古猿到智人
从费因曼的段子说起
这本书的副书名叫作“新著世界科学技术文化简史”。这个名字听上去有点儿长,而且似乎有点奇怪:如果单叫“世界科技简史”,好像还好理解,为什么还要加一个“文化”呢?科技和文化是什么关系?还有,在这个副书名的英文翻译(A New Brief World History of Science,General Technology & Culture)中,technology一词前面怎么还有一个 general?这是什么意思?
的确,按照史学界的学术规范,在讨论像“科技文化史”这样的概念之前,理应先给“科学”(science)、“技术”( technology)和“文化”(culture)都下个定义,从而再给“科技文化”下个定义,确定好它的内涵和外延,才方便之后的研讨。但麻烦的是,虽然大家对科学、技术和文化这三个词完全不陌生,但它们恰恰都是那种很难给出定义的词。这种困难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这三个概念所涵盖的现象和活动非常复杂多样,要把这么多现象和活动的共性和本质找出来,并概括成简单的语言,本身就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第二,即使有人辛辛苦苦给它们下了定义,其他人也可能不接受,而另外为它们下别的定义。因此这三个概念有很多不同的定义,如何在这些定义中进行抉择,同样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对于历史学这样的人文社会学科来说,因为缺乏像理工科那样的思想共识,上面提到的在同一个概念多种不同的定义中进行抉择的困难,就成了一个很突出的问题。美国有一位很有名的物理学家叫费因曼( Richard P. Feynman),博士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是 1965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他同时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科学通俗读物作家,晚年由他口述的自传《别闹了,费因曼先生!》非常有趣。书里面有一段,就体现了身为自然科学学人的费因曼对哲学概念在定义上缺乏共识的现象的嘲讽:
在普林斯顿研究院的餐厅里吃饭、聊天时,大家总喜欢物以类聚地坐在一块。开始时我也跟物理学家坐在一起,但不久我就想:看看世界其他人在做些什么,一定也很好玩。因此,我轮流和其他小组的人一起用餐,每一两个星期转移阵地一次。
当我转到哲学家的小组时,听到他们很严肃地在讨论怀特海(Alfred NorthWhitehead)所著《过程与实相》(Process and Reality)一书。他们的用语很奇怪,我不大听得懂他们在说什么,但我不想打断他们的谈话,唠唠叨叨地要他们为我说明,其实有几次当我真的问问题,而他们也试着解释,我还是摸不着头绪。最后他们干脆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研讨会。
他们的研讨会很像在上课,每周固定一次,讨论《过程与实相》的其中一章,方式是由某些人报告读后心得,之后再进行讨论。在参加这个研讨会之前,我拼命提醒自己,我只不过是去旁听,千万别开口乱说话,因为我对他们的题目一无所知。
研讨会上所发生的事,却是很典型的——难以置信的典型,但千真万确地发生了。首先,我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一句话也没说,这也是很难置信的事,但也真的发生了。接着一位同学就讨论的一个章节发表报告。在这一章内,怀特海不停使用“本质客体”这个名词,用法很专门,也许他曾在书中对这个词下过定义,但我完全搞不懂那是什么东西。
略微讨论过“本质客体”的意义之后,主持研讨会的指导教授讲了一些话,意图澄清观念,又在黑板上画了些像是闪电的东西。“费因曼先生,”他说,“电子是不是‘本质客体’呢?”
于是,我又惹上麻烦了。我解释说,由于我没有读过那本书,因此我压根儿不晓得怀特海所指为何,而且我只是来旁听的。“不过,”我说,“如果你们先回答我一个问题,让我多了解‘本质客体’这个概念,我就可试试回答教授的问题了。请问砖块算不算一种本质客体呢?”
……答案倾巢而出。有人站起来说:“一块砖就是单独的、特别的砖。这就是怀特海所说的本质客体的意思。”可是又有人说:“不,本质客体的意思并不是指个别的砖块,而是指所有砖块的共有的普遍特性,换句话说,‘砖性’才是本质客体。”另一个家伙站起来说:“不对,重点不在砖的本身,‘本质客体’指的是,当你想到砖块时内心形成的概念。”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起立发言,我发现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听到那么多关于砖的天才的说法。后来,就像所有典型的哲学家一般,场面一片混乱,好笑的是,在先前那么多次的讨论中,他们从来没有问过自己,究竟像砖块这类简单物体是不是“本质客体”,更不用说电子了!
实际上,怀特海的用词不是“本质客体”(essential object),而是“永恒客体”( eternal object),费因曼记错了。从哲学的角度讲,那三个学生对怀特海的“永恒客体”概念的理解也都不对。但是这些都不影响这一段故事体现的自然科学家从人文学科概念的不唯一性那里感受到的“荒谬”性。
同样,如果一定要在本书一开始就探讨科学、技术和文化这三个词的种种定义的话,那这本普及读物的开头就会陷入一些抽象的、过于学理性的讨论,读者会觉得太无聊了,摔书不读还是轻的,我怕的是以后大家可能会像费因曼那样对人文学科抱有终生的偏见。更何况,如果没有把对科学、技术和文化现象与活动的直观感悟作为知识基础的话,即使给出对这三个词的定义,给大家的印象也不深刻,大家也不容易记住。所以,最好还是先开始讲具体的、生动的史实,有了一定的史实基础之后,再回来总结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定义,这样比较有趣味,感受也会比较深刻。
那么,一部世界科技文化史,应该从哪里讲起呢?我们先来看两个现成的例子。美国学者詹姆斯 ?麦克莱伦三世( James E. McClellan Ⅲ)和哈罗德?多恩( Harold Dorn)合著的《世界科学技术通史》一书,在美国广泛用作这门课的教材,它的第一章先从由古猿到智人的演化讲起;中国学者吴国盛所著的《科学的历程》追溯得更远,是从宇宙的起源和演化讲起,其后当然也要讲人类的起源和演化。国内外的科技通史作者不约而同都把这个“故事”(英文 story,它和“历史” history是同源词)的开头放在人类的诞生或更早,这是因为,从人类诞生的时候开始至少就已经有技术或文化了,所以不先从几百万年前讲起是不行的。不仅如此,我觉得上述两部著作对从猿到人、从旧石器时代到农业出现前夕的这段历史讲得还太简略,人类社会中有些关键的要素,恰恰是在这段时间内奠定其基础的,只有充分了解人类的这段早期历史,才能很好理解此后历史时期中人类社会的各种现象。所以,这第一章将只讲农业以前的人类故事,第二章再讨论“三农”问题。
“生物学人类”的起源和人类的本质其实,“人类”(humans)这个概念也是没有统一定义的。我们先从生物学意义的人类开始吧——这是最流行、最容易被今天的人接受的一个定义。
“生物学人类”(biological humans)这个概念,是伟大的英国生物学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R. Darwin)在 19世纪中叶提出以自然选择为基础的演化论之后,才发展成熟的。今天,连很多普通的中国人都知道“人是猴变的”,可见演化论思想在中国普及之广。
不过,知道一种思想和能够正确理解这种思想 ,是两回事。一般人对人类演化的理解其实充满了错误。比如,严格来说,猴( monkeys)和猿( apes,也叫“类人猿” anthropoids)首先是指现代仍然生存的物种,而现生的猿猴里没有一种是人类的祖先。准确的说法应该是,从猴、猿、人的共同祖先中演化出了猴类的祖先与人猿共同的祖先,再从人猿共同祖先演化出长臂猿类的祖先与大猿(great apes,是猩猩、大猩猩、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统称)和人类的共同祖先,复从大猿和人类的共同祖先演化出大猿的祖先和人类的最近祖先——猿人,最后从猿人演化出人类。我们可以用动物分类学的语言把这个过程重述一遍:现代的猴类、长臂猿类、大猿和人类及历史上存在过的那些形似的祖先类群都属于灵长目(Primates)。首先,人猿共同祖先和其他灵长目动物的祖先分离开来,形成了人总科( Hominoidea,英文 hominoids);然后,长臂猿类的祖先分离出去,剩下的形成人科( Hominidae,英文 hominids);接着,猩猩的祖先分离出去,剩下的组成人亚科( Homininae,英文 hominines);再次,大猩猩的祖先,以及黑猩猩和倭黑猩猩的共同祖先先后与人类的祖先分离,三者分别形成大猩猩族(Gorillini)、黑猩猩族( Panini)和人族( Hominini,英文 hominins)。人族包含好几个属,其中只有人属( Homo)的各个种能够称为“人类”,它们是从其他那些“猿人”属演化出来的。这些关系用语言表述出来很啰唆,但画一张图便一目了然(图 1-1)。
图 1-1 灵长目的系统发育树
图片来源:根据麦格劳-希尔教育出版集团版权所有的图片翻译、改绘
这种演化关系是怎么确定的呢?原来我们和其他灵长目动物的亲缘信息竟然就藏在我们身体的几乎每个细胞里!乍一看,这可能会让人吃惊,但如果大家回忆一下中学时学过的生物学知识,就觉得并不神秘了。人体的绝大多数细胞都含有 DNA(“脱氧核糖核酸”的英文 deoxyribonucleic acid的缩写),也就是遗传信息的载体。这些贮存在 DNA分子中的遗传信息,在形式上体现为4种碱基(A、T、C和 G)的序列。但是,DNA上已经确定有意义的序列(也就是基因)只占其全长的一小部分,更多部分是目前还不知道其功能的序列。这就好比一本书里面我们能看懂的文字只占一小部分,几乎湮没在其他大量的乱码里面一样。 DNA中的这些无义序列既然不能“表达”成具有生物学功能的 RNA(核糖核酸)、蛋白质等物质,也就不受自然选择的影响,而是随机地发生突变。这个突变速率几乎是恒定的,在误差允许的范围内就像钟表一样准时——每过差不多一段相同的时间,就发生一次突变。因此,从共同祖先分离出来的两个种的同一段 DNA无义序列差别越大,它们分离的时间越久,亲缘关系越远,而且具体的分离时间是可以通过序列的差异程度推算出来的——这就是“分子钟”(molecular clock)测年法。
正是通过用分子钟方法比较人和其他灵长目动物的 DNA序列,我们不仅能够确定现生灵长目动物之间的演化关系,而且能够大致确定它们的祖先相互分离的时间。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还在 8500万年前的晚白垩纪,那时恐龙还没有灭绝,灵长目的祖先就已经和其他哺乳动物的祖先分开了;大约 3000万年前的渐新世,人猿共同祖先和其他灵长目动物的祖先分离;到 1500万~ 2000万年前的中新世,长臂猿类和人科分离;大约 1400万年前,猩猩的祖先和人亚科分离; 600万~ 800万年前,大猩猩族分离出来; 450万~ 600万年前,黑猩猩族与人族分离开来,到这个时候,人类祖先就和所有 4种大猿的祖先“相揖别”了。
现在让我们来看人族这个分支出现之后的演化过程。已知人族最早的属可能是萨赫勒人属(Sahelanthropus),是 2001年在乍得境内的萨赫勒地区(撒哈拉沙漠南部的一条荒漠草原带)发现的。根据专用于化石年代测定的一套办法,人们测出萨赫勒人生活在 600万~ 700万年前,这几乎与上述用分子方法算出的人族和黑猩猩族分离的时间同时。因此,如果萨赫勒人的确是人族成员的话,那它就代表了人族的最早阶段。不过,也有人认为萨赫勒人可能是人和黑猩猩的共同祖先。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