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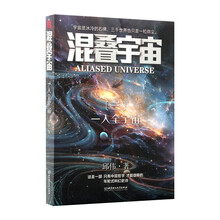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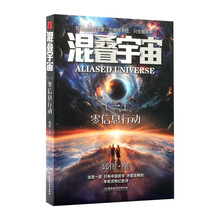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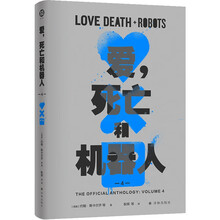

美国销量过百万的科幻小说,一人双魂的奇妙世界
一个强烈渴望认可的新颖故事;技艺娴熟,描述栩栩如生
——Lissa Price
令人震惊的du家故事重新定义了人类的含义。
—— Lauren Destefano
要是艾迪和我在五岁的时候“解决”了,又会怎么样?我会消失,艾迪的生活会大不相同。没有医生预约,没有治疗专家,没有药物。操场上没有侧目回避。没有老师的窃窃私语。没有诺南德,没有波瓦特,也没有汉斯……
把书藏在课桌下面, 天黑之后仍久坐不起的读者。最终,我们的生活都是故事。
——凯特·张
序 言
追忆童年,很少有人比得上我。一般说来,人们长大就有了自由;我却失去了自由。
我是隐性人,生来比艾迪弱。每每当我们争着要为共有的躯体做主时她总是赢。她注定会赢,而我必输,前途已写入我们的基因。
我们十二岁的时候,我似乎即将落入隐性人注定的命运:消失。但我并没消失,只是失去了一切自由:不能说话,无法走动,无权得到他人的认可,除了与我共享躯体的艾迪之外。
因此我对童年记得很清楚。因为尽管长期受到约束,那却是我对自由仅有的记忆。
直到遇见丽萨、哈莉、赖安和戴文,我才开始思考未来,而不是过去。他们也是双生人。他们明白藏在暗处生活意味着什么,还教我如何重新掌控自己的躯体。
可现在,我们全都再次被迫不停地奔波,为了安身,东躲西藏。我重拾儿时记忆,想起那万般好处,种种温情,在陈年往事中寻得安慰。
想什么呢?一天夜里艾迪问我。我们都被塞进车里,彼得开着车,莱安纳医生坐在旁边。我们其他人坐在后面两排,肩膀挨肩膀,挤作一团,车窗摇上来,关得紧紧的,把冷风挡在外面。
罗盘星。我说。
我的童年回忆也是艾迪的回忆。我们被劈成两半,相依为命,一个双生人,活在一个不给双生人合法身份的国家。
知道罗盘星的时候,我们还不懂这些,因而那段回忆弥足珍贵。那时艾迪和我三四岁年纪,我们全家去野营。我们的小弟莱尔还没出生,所以只有我们四个人:妈妈、爸爸、艾迪和我。
我记得第一次在山中吸着清新的空气所看见的星星的样子。此前我们这些孩子看惯了城市的夜晚和灯光。那些星星大得让我们吃惊。
记得吗?我说,过去我们露营时爸爸总给我们讲那些星座,不过他老是……
老是一点也想不起罗盘星的故事。艾迪说。她的微笑将我们的嘴唇拉成一条弧线。那是在我大脑边缘的一种温暖,在那里我把握十足地感受到她的存在,就像感受自己的心跳一样。我记得。
我们陷入回忆,当大路飞驰而过时以回忆相互慰藉。
一切太快,一周过去了。接着是一周又一周。艾迪和我慢慢可以走路了,我们脚踝和身上的伤痛以及最后几天在安绰特的痛苦回忆也渐渐消退了。波瓦特研究所的爆炸——警察突袭——穿过昏黑的街道仓皇逃跑——这些记忆永远不会彻底放手,将一直缠着我们。但是我们试图用幸福的回忆遮掩住那些痛苦。
艾迪和我引着大家讲故事。四处藏身,不知身在何方,几乎无事可做。刚开始我们一直看新闻,但电视屏幕显示出我们的脸的样子以及我们的名字,不厌其烦地播报我们的罪行:兰开斯特广场“爆炸”和波瓦特爆炸。过了一段时间,恐惧和不安潜入我们的内心,侵蚀我们。艾米利亚说:“他们老是讲同样的事情,一遍又一遍的。把它关掉行吗?”
于是就关了。不过呢,我们却聚在楼上的走廊里,或是围在餐桌旁,或是躺在露出线头的长沙发上。如果是由赖安和我做主,我们就试着挨在一起,互相取暖,我把脸颊靠在他的肩膀上,寻求那种有人在一起的安慰。
我给他们讲莱尔和纳撒尼尔出生那天的事儿。艾迪和我只有四岁,但我们忘不了那幸福而紧张的忙乱场面。婴儿裹在蓝布里。妈妈生的不是女孩,这让我感到一阵失望。
我没给他们讲那天纳撒尼尔逐渐消失的事儿,人们觉得正常,因为他是隐性人。也没说莱尔生病那天的事儿,他们急匆匆地送他去医院——他脸色苍白,一个小孩子,吓得说不出话。
我们有条不成文的规矩,伤心事免谈。
那种事已经太多。
关于赖安的过去我知道很多,但是再听一遍也无妨。乡下巨大的老宅子,穆兰一家搬到鲁普赛德之前就住在那里。古老的地板咯吱作响,图书室永远满是尘土,那块连成一片的田地里长着齐腰深的草,黄昏玩战争游戏时正好作掩护。哈莉或是丽萨插话补充几句,要不就抱怨说他没有完全说实话。赖安表示抗议,但他微笑着, 我知道他并非真的介意。哈莉或丽萨的插话把我们逗笑了,现在的笑声可太珍贵了。
莱安纳医生被大伙哄着也讲了个故事。起初,她只是说了些自己年轻时的事儿——倍受呵护的童年时代零碎的片断。我看着她脸上明显的皱纹,试图想象出二十年前她小时候的样子:不是一个妇人,而是一个名叫瑞贝卡的小女生,她那少年老成和过分严肃的面容让大人们觉得好笑。她知道她的兄弟彼得所隐藏的那个秘密,却严守死防着。
最终,我们用甜言蜜语套出了有关她在医学院上学时的趣事。不过我们得小心,不要问她有关离开医学院以后的事儿。莱安纳医生将药品方面的研究与她擅长的神经学紧密联系起来,为此她进入诺南德精神病康复医院,在那儿她遇到了杰米,然后是我们其他人。在那儿艾迪和我说服她背叛同事,帮我们逃跑。
大家最喜欢亨利的故事,因为他见识过这个世界。特别是杰米,当亨利描述他所去过的地方、经历过和写过的事情时,他就盯着亨利的那些地图钻研。
“你写过我们吗?”一个有关中东的故事讲到一半的时候凯蒂问。亨利在那里待了两个月,追踪我们从未听说过的两个国家之间的边界战争——我们在学校里上课时所教的那些过时的地图上根本就没有。
“我的意思是,专门关于我们的。”
亨利笑了。“没有提名字。那样更安全,以防备东西被人截住。”
不知怎的,我从来不曾冒出过这种想法。我知道亨利跑来这里是为了报道美国双生人的困境,通过卫星电话——比电话还要小的微型计算机,我认为——发回文章和信息。不过我却没想到他的故事一点也不笼统。
这个想法我一直有。外边那里某个地方,或许有人听到我们的故事,或许仅仅是——早晨喝咖啡时的一个故事,或是晚餐时起个背景的作用。仅此而已。
很奇怪,是不是?我对艾迪说。
你想多了,伊娃。她回答。
但这由不得我。好多年了,那时我还没有重新掌控我们的身体,我什么也干不了,除了思索和想象。这会儿,我想象生活可能会是怎样,如果艾迪和我生在大洋对岸的某个国家,在那里双生人受到认同,属于正常。
或者要是艾迪和我在五岁时“解决”了,又会怎样?我会消失,艾迪的生活会大不相同。没有医生预约, 没有治疗专家,没有药物。操场上没有侧目回避。没有老师的窃窃私语。没有诺南德精神康复医院。
没有哈莉和丽萨, 没有赖安和戴文,就没有那之后我们遇到的所有人。
艾迪和我离家去诺南德才不到一年,生活却已经天翻地覆,很难想象出我们的未来将会怎样。当初若是我们守住秘密,就没人知道我的存在,可是艾迪脑袋里的灵魂,喊声太大,包不住。
现在我们有许多时间坐下来思考。不过聚集美好的时光,回想我爱的人们和与他们在一起的精彩瞬间,心里甜蜜蜜的。
我的母亲和父亲,我确信他们依然爱我。
我弟弟,莱尔,我对自己说,他已经做了政府向我家里人所许诺过的肾脏移植。
我又想起了塞宾娜和乔希,回想她们坚定的眼神,她们只消看我一眼就会在我体内注入信心。我眼前现出科迪莉亚和卡蒂笑的样子,头向后仰,淡淡的金色短发在光亮中轻若柔羽。我打定主意,只想克里斯托弗的柔情时刻,他那鲜亮的盔甲上有条裂缝,透露出他过去的零碎散片,一路掘进他的内心深处。
我看见杰克逊——杰克逊和文森,诺南德医院的邮递员,他们告诉我心存希望。
我本不该去想我们和塞宾娜那帮人一道做过的那些事。我们用自制的爆竹在兰开斯特广场造成的混乱场面。我们帮着制定的炸掉波瓦特研究所的计划——那时我们不晓得,塞宾娜想要炸开的不只是钢筋水泥,她还想要当晚那些官员的性命。
当我们发觉时,想制止那一切,于是内部出现纷争。
我们付出了代价。
伤心事免谈。那是规矩。
亨利应该离开我们的那一天,艾迪和我醒来时听见新闻主播正在轻声地叽里咕噜播报着什么。我们蹑手蹑脚地从凯蒂和哈莉身旁经过——俩人都还睡着呢,然后溜出我们共享的卧室。
戴文在楼下坐着,正是破晓时分,半明半暗,他眼睛紧盯着那台微型电视。屏幕在客厅投下奇怪的、闪着亮光的影子。没见到其他人。
“他们还没走,是不是?”艾迪一边小声地说着一边凑近戴文,也坐到那个高低不平的长沙发上。他眼睛没离开电视,只是摇了摇头。
他们人在哪儿?我问,艾迪正要大声重复我的问题,这时亨利的卧室门打开了,正好做了应答。
亨利冲我们微笑,他的牙齿在深色皮肤的映衬下闪出一道白光。“我以为昨晚我们已经道过别了,所以你们用不着起得这么早。”
他随身只带了一件小行李箱。我们逃离安绰特时他的大部分东西都扔了。我想象警察找到那些东西了,用步枪扫射他的笔记和写了一半的文章。现在他们应该明白了要监视他。一个外国记者生活在美国面临许多危险,在海外的朋友和家人的压力下亨利终于让步,准备及早飞回国。
他斜靠在沙发靠背上,好看清楚电视。“又是詹森?”
戴文点头。这是一个旧片断。过去几个星期马克·詹森做了好多演讲和访谈。有关双生人。有关波瓦特。有关国家的总体安全。
很难将他在电视中面对世人的样子——处变不惊,得体自信——与艾迪和我扭伤脚腕之后想要将我们带离波瓦特的那个人联系起来。爆炸之后那个人从废墟中挖出我俩,他眼神狂乱,衬衣上沾着血。
每当我看见他,就感到肩上隐隐作痛——他的指甲那时曾掐进我们受伤的皮肤。“那个男孩在哪儿?”他冲着我们喊,“杰米·科塔在哪儿?”
“他是想控制局面。”在不了解戴文的人看来,他好像对整件事感到厌烦了。但是我捕捉到他的眼睛敏锐地追随詹森的一举一动的样子。戴文往往是我们之中最具观察力的,因为他举手投足间仿佛世界只是一幕不大有趣的皮影戏。
“似乎控制局面不是詹森该管的事儿。但我猜他应当是双生人问题的专家。”亨利直起身,戴文终于将眼光从电视机挪开。他的脸保持着惯常的湖水般的平静,但是当亨利说“好吧,我估摸着该走了”的时候,它泛起了涟漪。戴文和赖安醒得早,但是凌晨四点早得有点过了头,这时候起床不会只是心血来潮。
“给——”亨利手伸进口袋,取出卫星电话,递给戴文,“你记得怎么用,对吗?”
戴文已经把手机拿在手里转来转去,查看那差不多是手掌大小的屏幕,微型键盘,以及与计算机连接的端口。他边摆弄天线边点头,然后抬头回看亨利。“你不用吗?”
亨利耸了耸肩。“用不了几天我就到家了。我已经给我的人说过在我到之前别等我的电话。另外,我需要一种与你们大家保持联系的方式,”他微微笑了一下,“不过,要小心。这些东西并不是没办法追踪,要是政府起了疑心。要限制通话次数。而且别让赖安给拆掉了,他也许没法再弄回原样。”
戴文差点就要咧开嘴笑了。“我能弄回原样。”
我在大脑的那个角落里偷着笑,想知道赖安对此是怎么说的。
后门开了,艾米利亚和彼得出现了。见到艾迪和我立在那儿,艾米利亚似乎并不吃惊,彼得却扬了一下眉毛。
“我们走吧?”艾米利亚说着,把外衣紧紧地裹在身上。她和苏菲,自告奋勇开车送亨利去下一个州找他的联络人,她们争辩说自己是最佳人选,因为新闻上没有出现过她们的脸。还有凯蒂和妮娜同样没有被曝光。
杰米的信息已经在媒体上流传了数月。在我们所有人当中,他是詹森最急于找到的那个——诺南德的医生手术剥离了他的第二灵魂时,这孩子大难不死。
但詹森也在波瓦特看见了赖安和莱安纳医生,当时我们想制止爆炸,然后他们过来救艾迪和我。他一定是凭直觉意识到哈莉会和她的兄弟在一起,而且警察突袭将会发现把亨利和彼得列为嫌犯的充足罪证。
让他们全都因为爆炸事件而受牵连,这令我痛苦。
“路上小心。”彼得说。他和莱安纳医生将和我们一起待在安全之家这里,以防出事。那个词现在每时每秒都悬在我们的生活里:以防出事。
亨利最后一次看了看我们和戴文,像是他想记住我们的容貌。
“祝平安。”他说,走向门口与艾米利亚会合。
他们离开了,留下我们其他人目送他们。
“我没想到你会不叫醒我。”几小时后,哈莉这样对赖安说。她在室内的阳台上挨着艾迪和我坐下,俯瞰起居室和门厅。我们的腿搭在沿上晃来晃去。
赖安坐在我们的另一侧,他伸手穿过阳台的横档去偷哈莉的半个花生黄油三明治。她手向旁边闪,晚了一秒,一脸的委屈。
“那会儿是早上四点。”赖安让我咬了一口三明治。花生黄油流到他的手指上,他把手指放进嘴里,说出来的话含含糊糊的。“你不喜欢在十点之前起床。”
“要是你们其他人起来了我也会起床的。”她抱怨。
回想当初,我简直不敢相信,艾迪和我在学校的走廊里经过戴文或是赖安的时候,几乎从没注意到他们。我们还曾绕路躲开哈莉,因为我们害怕她的外国长相会给我们招来麻烦。
现在,他们算得上是我的生活中最重要的人。
我盯着赖安看得久了那么一点,他扬起眉毛,嘴角牵动笑了一下。“怎么了?”他说。我摇头,自己也笑了。
我们擅长用眼神交流,或是碰一下,咧一下嘴。小动作是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安全之家太小了,即使我和艾迪不共享身体,也找不到时间和地方让我和赖安能单独在一起。
有时候,艾迪会提出要潜隐。但负疚感通常让我拒绝她。艾迪的脑子里也装着一个男孩。眼下若是有他在,他会在走廊的尽头偷偷吻她,笑着,不在乎艾米利亚路过时看着我们,一副什么都知道的样子。
哈莉吃完三明治,站起来,掸掉衬衣上的面包渣。“好呀,要是——”
门铃响了。
哈莉的嘴啪嗒一下合住了。艾迪低声说:可是没人——
有人按门铃。这所房子并不比我们住过的第一家偏僻,可还是离最近的城镇有将近一个小时的路程。没人会碰巧找到我们门口来。
莱安纳医生从楼下她的房间出来,她刚冲过澡,头发还湿着。她仰头示意我们安静的时候,所有要说的话都写在脸上。
彼得走到门厅,拉住他妹妹。窗户全都挂着窗帘。我们乘过的那辆车停在车道上,所以我们没法假装房子里没人住,但是可以假装没人在家。
好长时间,没人说话。没人去开门。
门铃又响了。接着开始敲门。门上响起刺耳的敲击声。
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
“打扰了,我是玛丽安·普里特,我想找艾迪·塔姆辛。”
2
莱安纳医生打手势,让我们退出去,我们与其他人一起撤到我们的卧室,我们的心咚咚地跳。我倒在床上,双手把那条破旧的被子攥过来攥过去。
哈莉最后一个进来。“你以为你是谁呢?”她关门的时候嘀咕着。赖安站在我们身边,他身体绷得紧紧的,满是忧虑和疑惑。
当然,谁也没主意。我们的照片漫天飞,现在可能人人都知道我们。镇静,我一个劲地命令自己。我屏气凝息。不能乱了方寸。
艾迪和我并不是第一次经历恐慌,七岁之后我们就有了这种经历,熟知狭小空间里的那种恐惧滋味。但是在波瓦特之后那几个星期,其他事情也开始让我们躁动不安——突如其来的噪声、阵阵热浪。
有时候,只不过是想到了黑暗、痛苦,害怕我们被埋在一截倒塌的墙下,残骸被火焰吞噬。
那个女的要是想抓我们,我对艾迪说,她用不着敲门。
天知道她想干什么,伊娃。詹森知道我们在安绰特——知道我们有所计划——他始终不接近我们,直到他知道自己能造成最大的伤害。
哈莉把手放在窗台上。“她的车不错。”她眯着眼,将黑色的卷发从脸上撩开,“看不见车牌——哦,后座有个女孩——”
赖安和我们急忙跑到窗边。在我们的注视下,那个女生打开车门爬了出来。她看样子大概十二岁,比凯蒂和妮娜稍大一点。她急匆匆地向房子走去,大衣在风中飘动,她迎着寒风缩起了双肩。
要是那个女的想抓我们。我说话的时候多了一丁点把握,她为什么还带个小孩?
“你以为她们是双生人?”哈莉说。在安绰特的组织彻底土崩瓦解之前,常常有人来找彼得帮忙。他们从朋友的朋友那儿听人说起他,人们私下传言说他统领着一个双生人和同情双生人的组织,他兴许能把孩子送到安全的地方,甚至还能将孩子从研究所营救出来。有那么个人,表明在那儿或在某个地方还有希望。
窗外那个女生仰着头直视我们。
她的脸上有某种东西似曾相识。
她肯定是认出了我们的脸。她双眼睁得大大的,张着嘴巴。风把她的脸颊吹红了。
我们怎么会认识她?我对艾迪低声说。
赖安与我俩手指相扣。“怎么?”
“我以前见过她,我觉得。”不由自主地,我攥紧他的手,“我——我记不起是在哪儿。”
彼得走进我们视线,他招手叫那个女孩过去。然后他跟着她的目光,将视线落在我们身上,接着又转回去看那个孩子。她一直想要偷偷地往上瞧,但是他把她领进去了。
我在记忆里狂乱地搜索。
不在学校。艾迪说。我还没来得及想那么远。这个女生的脸在记忆中比那要晚。
“在安绰特?”赖安问,但他好像很迟疑,我摇头。记忆就悬在大脑的边上——
“她不在诺南德。”哈莉的声音里显出确定无疑,没人争辩。我记得我在诺南德认识的每个病人的脸,虽说过了这么多个月,微小的细节已经模糊不清。这个女生没和我们一起穿过蓝色制服。
卧室门口响起一阵很轻的敲门声。
“是我。”彼得说,然后马上就推门进来了。
他这会儿的样子看起来和往常一样,好像要把世界捏成团攥在拳头里。有时我希望能够见到他就如那晚在诺南德救我们的样子。那时他和杰克逊在医院门廊的一片黑暗中化为童话故事里的英雄,引导我们走向光明和自由。
现在我更加了解他。他只是一个人而已,想要的很多,能做的却不多。
赖安不情愿地放开我俩的手。我跟在彼得身后,同时看了赖安一眼以示安慰。我们穿过大厅,来到他和艾米利亚同住的房间。和房子里的大多处地方一样,这里有股锯末和木材清漆的味道。
“我以前见过那个女生,”彼得一关上门我就说,“我记不起是在哪儿,但是——”
“她名叫温迪·霍华德,”彼得说。我皱眉,这个名字在我们的记忆里没有印象。“我想你以前没有见过她。”
“见过,”我坚持道。“我认识她的脸——”
彼得伸进口袋掏出一张折起来的纸,他把纸放在桌上抚平打开,“你确信你想起来的不是这个?”
我愣住了。艾迪的反应更多地表现在内心,但她不在掌控,所以显不出。但我却感受到了——冰冷尖锐的刀锋——对着我。
那张纸是个传单。当时我们制作这些东西时就这样叫,还从兰开斯特广场周围那些建筑物上把它们往广场撒。
彼得说得对。我们从没见过温迪·霍华德。不过这画画得太像了,让我顺着脊椎骨直冒凉气。
“温迪随身带来的,”彼得说,“这是你的,对不对?”
我点头。我还在盯着那张传单看,看我们用双手不辞辛劳为那个女生画出的那张画像。
“我们为……为兰开斯特广场做的。”我轻轻地说。我们告诉过彼得和别人这件事。塞宾娜如何招募我们帮她在集会中间分散群众注意力,好让她和戴文溜进市政委员会,收集政府有关波瓦特研究所的计划和资料。“所有的传单上面都有双生人儿童的画像……”
我用我们的手指摩挲安娜·H,十五岁的脸上印的那些字:
有多少孩子死于这一治疗?
很奇怪,想起我们曾经是那样地满怀希望,想起我曾经是其中的一员,感到无比的轻松和高兴。
你画得真棒。我低声说。
艾迪没说别的,只一个劲地念叨着科迪莉亚的名字。安娜和科迪莉亚曾经一起在某个研究所里待过。它和楼下的那个女生看着很像。艾迪身体发抖,但那不可能是安娜。
安娜·H死了。
我们的传单选的都是死去的孩子。
彼得把传单折起来,背面朝上。也许他注意到我盯着它看的那个样子——知道只要把它摊在桌上,我就会什么也想不出,满脑子都是艾迪和我在塞宾娜和科迪莉亚的照相馆上面那个阁楼里度过的时光。那天,我从艾米利亚的公寓溜出去,怀着一种责任感,懵懵懂懂地,拿上一捆传单和一个自制的鞭炮,上到俯瞰广场的楼顶。
那些传单怎么会有一张到了温迪·霍华德的手里?那天早晨她在那里?还是传单过了一道又一道手,最终到了她的手里?
“温迪说她是安娜的妹妹。”彼得说。
“双生人?”
他摇头。我挣扎着想摆脱有关兰开斯特广场的回忆。鞭炮炸开,劈里啪啦作响。人群吓得嚷声一片。没时间想伤心事,即使我自己的大脑也不行。“和她一起的那个女的是谁?她叫玛丽安?”
“是个记者,”彼得说,“她说她想做一个有关安娜和温迪的有人情味的故事。关于双生人全体的。她想为我们的事业出力。”
有人情味的故事。这些词在我的头脑里没有意义,支离破碎的,连不成一个能让人弄明白的整体。人情味。那意思是她认为我们的故事有趣?或者她指的是一个有关人类利益的故事?我们的利益?我们想要的自由和安全之类的恩赐?这些对于那么多别的人来说,不只是让他们关注,而且是他们的权利。
这可能是个花招。艾迪说。要是说从过去的几个月里我们学到了什么,那就是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政府和媒体紧密地勾结在一起。她为什么站在我们这一边呢?
“她为什么来找我们?”我问。
“因为她知道自己在冒什么样的风险。”彼得盯着立在卧室墙的四周一排排发霉的架子,他的手掌平放在书桌上,肌肉紧绷着,“如果她被发现了,政府会抓她的。她需要人把她藏起来,保护她。”
“你认为她真的想帮我们?”
他犹豫了。“也许吧。或者她只是想帮她自己。如果事情……如果事情有好的结局,她就有了一辈子都讲不完的故事。”
“我们能信任她吗?我的意思是,温迪……温迪或许真的是安娜的妹妹,不过……”
“但那也说明不了什么,”彼得说,“温迪的姐姐是双生人并不意味着她就不会利用那个事实帮着迫害其他双生人。”
他说话的时候是那么无动于衷,那么简洁明了。温迪·霍华德还只是个小孩子,不过也许那正好说明她更容易被操控。
“那么,为什么她们还在这儿?”我有气无力地说。
彼得低声笑了,声音不大,蔫蔫的,但依然还是笑声。“玛丽安有备而来。她有我们需要的东西,她明白这一点。”
彼得看我们的样子透露了一些什么。警铃在我们胸中响起,敲打着我们的心。
“什么?”我说。
他停了一下。仿佛他需要一点时间让自己相信无论他说什么艾迪和我都能够应对。
“怎么了,彼得?”我追问。
“是杰克逊,”他说,“她说她知道怎么救杰克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