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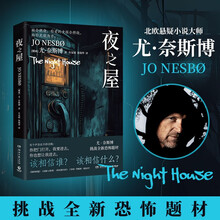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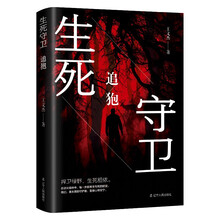




“美国私家侦探小说作家协会”甄选的首奖作品
书稿受到侦探小说家S.J.罗岚的称赞
纽约时报多位畅销书作家联合推荐
“芭比娃娃谋杀案”,死者都是年轻貌美的女子。警方在很快的时间破了案,抓住了凶手。但是,一个女人却找到了克莱顿这个小个子私人侦探,声称凶手另有其人,委托他为死去的妹妹抓住真正的凶手。克莱顿接下了这个委托,带着助手蕾切尔开始堪巡真相。在两人调查的过程中,疑点层出不穷,危险也随之而来,每一次死里逃生都离真相更近了一步。最后,两人竟发现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一个非常合理、确定又令人吃惊的人……
1
从曼哈顿中城第34街上传来的汽车喇叭轰鸣声,透过了一间矩形办公室远端的两扇高大窗户。蕾切尔·瓦斯克斯感到心烦意躁,但她的目光只是越过那杂物堆积如山的办公桌,扫了她的老板克莱顿·格思里一眼,便又重新回到她的电脑显示器前。这位来自波多黎各的年轻女子已经为这位小个子侦探打了三个月的工了,但他好像没接到多少正经的侦探活儿。在春天找到这份工作时,蕾切尔把它视作上帝的礼遇,可如今它就像一道枷锁。克莱顿·格思里简直是个疯子。三天前下班回家的时候,瓦斯克斯一心想要辞职,但她最终也只不过是想想罢了。
那个早晨的任务一开始显得一帆风顺。瓦斯克斯驾驶着格思里的蓝色福特,两人正在曼哈顿下城跟踪一对夫妇。男的是个身材矮小、肌肉发达的意大利人,毛茸茸的黑脖子上挂着一条闪亮的金链子。他周身仿佛笼罩着一层制胜者的光芒,可以像摆弄棋子般使唤身边的人。瓦斯克斯觉得他很招人讨厌。至于女的则身材高挑,淡棕色的头发在阳光的抚摸下闪着黄油般的光泽。她在这个意大利人面前搔弄着自己圆润的曲线,仿佛一份礼物,包裹在白色的短裙和蓝色的紧身上衣里,她一脸不爽的表情,只有在男人看她的时候才挤出一丝笑容。
瓦斯克斯觉得这对夫妇很像黑帮漫画里的人物,但格思里却清醒得像是公务员一般,一边盯梢,一边跟拍。这两位侦探像特勤局的特工一样耳朵里塞着对讲耳机,而瓦斯克斯开车时还在她的夹克衫口袋里别着另一枚摄像头。
整个上午,这对夫妇都在苏豪区和特里贝克区的商店慢慢闲逛,然后在布隆街街角的一家高档烤肉馆落脚享用午餐。他们落座的桌子在餐馆靠外的角落,透过两边沿街的窗户都能够清楚地看到。格思里让瓦斯克斯待在布隆街一家鞋店前继续跟拍,他自己则迅速绕过街角,从另一条街道取证。那位满脸怒气的意大利人和他皮笑肉不笑的夫人坐定后开始点菜。瓦斯克斯则按部就班地拍摄着。她这一处的视线非常清晰,连那个男人喋喋不休的嘴里的每颗金牙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饭吃到一半时,意大利人打了个电话。街道上车辆不多,多是一边走路一边打电话的雅皮士。瓦斯克斯为了打发时间,开始猜测哪些路人会走进那家烤肉馆,还数着有多少辆计程车在空载行驶。她瞧不上这种监视活儿。格思里听烦了她的喃喃自语,问她是不是更乐意去开计程车,好让她知道她的麦克风还开着呢。又过了好几分钟,瓦斯克斯突然意识到,餐馆里的那个意大利人已经注意到她了。他开始大笑并用手指着她。他的夫人转身向这边投来目光,而瓦斯克斯录下的最后一段影像便是她脸上惊怖的笑容。
一位身材魁伟的意大利小伙子抓住了瓦斯克斯的右臂拽着她团团转。“喂,我说!”他带着开心的语气大声嚷道,“你在干什么呢?”他下垂的髭须盖住了大半边嘴巴,脸粗糙得像块混凝土砖块,肌肉盘结的肩膀则像是一道拱门。他的身旁站着另一位身着慢跑服的意大利小伙子。这位的身材尽管没那么魁梧,脸上却带着同样顽皮的表情。
“放我走!”瓦斯克斯要求道。接着,她为了强调她的意思,用膝盖对准了他的胯部,但他却扭过大腿转向了一边。
“我们可碰上个斗士。”他低声道。就像往常一样,一些路人耸起肩膀快步离去,而另一些则伸长脖子想要看个明白。扭打很快就结束了,两位意大利重量级选手没花多少时间就把这个梳着黑长马尾、骨瘦如柴的波多黎各女孩子给制服了。他们要的是摄像机,而且成功拿走了。格思里赶到时,瓦斯克斯的耳朵还在嗡嗡作响,但她抓住了那个大个子恶徒的手腕,想要越过他长长的手臂给他一拳。
那个蓄着髭须的意大利大个子把瓦斯克斯甩到鞋店的玻璃窗上,但他冲向格思里时却突然打了个趔趄。瓦斯克斯看着格思里收回的手里空空如也。随着一声巨响,那个意大利大个子四脚朝天滑倒在地上。
“唷,戴夫,发生什么了?”他咕哝道。
格思里跨步走向另一个恶徒,夺回了瓦斯克斯的摄像机,然后俯身从这个男人的脸上拾起了自己被弄皱的棕色软呢帽。就在这两个意大利人挣扎着想要站起来的当口,瓦斯克斯也挣扎着从鞋店门口的玻璃窗前起身。她又能听到车来人往的声音了。她朝他们踢了几脚,尽管力道不大,两个意大利人则沿着人行道狼狈地爬走了。看热闹的围观群众爆发出骂声和嘘声,一位牧师从鞋店里冲了出来。
街对面的那对夫妇正透过烤肉馆的窗户看着这一幕。那位意大利人满脸愠色,一边指着他们一边对着手机大喊大叫。七月炽热的阳光照射着布隆街的街心,而格思里恰好站在人行道的阴影里,他掸掉软呢帽上的灰尘,把它恢复原来的形状。他看向帽子的内里时,面部因为嫌恶都扭曲了,丝质的内里被新鲜的血斑给污染了。他把帽子在腿上拍了拍,没有戴回到头上去。
他们回到那辆老福特里时,这位小个子抬起了瓦斯克斯的下巴,满脸阴云地审视着她的面庞,“你还不赖嘛。”他说道。
她甩开他的手,发动了汽车,她的正后方停着一辆巡逻警车,她驶出停车位后便进入了布隆街街角的十字路口。她用手背擦了擦仍然刺痛的鼻子,看看有没有出血。
“你怎么一点都没发觉就让他们偷偷接近了?”格思里问道,“我还以为你是在下东区长大的呢。”
“你真是脑子有病,老家伙。”瓦斯克斯吼道。“他们能逮到我,是因为你根本没提醒我要小心!那人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也可能是你光顾着在数计程车?”
“去你的。你本该告诉我他有眼线。话说回来,你干什么要监视他?”
“我们监视的是那个女人。”
瓦斯克斯狠狠地在方向盘上敲,倒出一堆西班牙语的骂人话。侦探笑了,用一些她没用上的骂人话顶了回去。原来他会说西班牙语,这个发现让她闭了嘴。
“也许我是本该把我的一些疑虑告诉你。”他过了一会儿说道。老福特车驶过了华盛顿广场。“又或许你更该小心谨慎。他注意到你了,所以你已经搞砸了。推卸责任不能掩饰过失。你得明白这一点,蕾切尔。这是门苦差事,但我对你有信心。你是个聪明的女孩子。你会明白怎么做的。”
瓦斯克斯回到家时气愤不已,她想做完下一项调查就辞职,但她却完全忘了脸上有伤痕这回事。那天晚上,在她父母的廉租公寓里,《公告牌》的广告都显得不再那么有吸引力。甚至连她的两位哥哥都很安静,一脸震惊与愤怒地盯着她的面庞。爸爸又重述了一遍她得申请读大学的二十七条理由,说完后用手指无声地指着她的脸。就在那个时刻,她发现她决心要继续为克莱顿·格思里工作。晚些时候,当整间公寓都安静下来的时候,瓦斯克斯的母亲来到她卧室敞开的门前。她安静地伫立着,仿佛构思着想要吐露的话语,最终只是叹口气,安静地走开了。
就这样,蕾切尔·瓦斯克斯并没有中途退出,而她马上就得到了任务,她得回去研究那些监视录像带。研究完后,小个子格思里跟烤三明治一样拷问她有没有注意到他希望她注意的所有细节,尽管他事先并没有告知她需要注意哪些要点。克莱顿·格思里非常疯狂,而他办事处的宁静也快让瓦斯克斯发疯了。至少办事处下面第34街上传来的喇叭轰鸣声意味着这个世界仍然在运转,孩子们正推着衣服架子过街,阻缓了交通的行进。这样的情形每天都在时装区发生着。她又越过堆满杂物的办公桌扫了格思里一眼。然后有人敲响了办事处的外门。
瓦斯克斯的目光越过一件胡乱摆放的家具,看到一个身影,填满了外门的整面毛玻璃。门随着一阵短促的敲击应声而开。一位一头银发、身着浅灰色西服的高大男子走了进来,身后跟着一位身着海军蓝连衣裙的年轻女子。格思里把手头的杂志放回到书桌上。“下午好,惠特里奇先生。”他招呼道。
办事处非常敞亮。每张办公桌都对着一张沙发,中间放着一张低矮的咖啡桌,上面摆满了图书和杂志。瓦斯克斯的桌对面是一面刷成绿色的灰泥墙,墙中间是那扇嵌着毛玻璃的外门,此外还有张年代久远的深红色皮沙发,让人想到这个房间也有过体面的时候。而高窗视线内的那张破旧沙发,用的则是棕色的人造毛皮面料。墙上黑色的木质护墙板(中间被外门隔断)和格思里身后的两扇黑色木门(一扇是储藏室的,一扇是盥洗室的)也让人回想起已经消逝的那个贵族年代。
一头银发、身材高大的惠特里奇先生虽然看起来和格思里一般年纪,都是人到中年,但他衣着讲究,气度不凡。他的灰色西装就像一名将军的军装般笔挺合身。而同样的年岁却让格思里看起来皱皱巴巴的。格思里身材矮小、体形单薄,尽管他那头军人的短发还是黑色居多,但身上却笼罩着一层沉重的灰色。他的桌头放着一顶深棕色的软呢帽,身上穿着一件白色的长袖衬衫,别在黑色的裤子里。惠特里奇绕了进来,坐在深红色的沙发上。这个高大男人的坐姿和一举一动都带着贵族的完美姿态;反衬得格思里就像个工人,满身都是闲散懒汉的标志特征。
瓦斯克斯的头上斜戴着扬基队的棒球帽,下着蓝色牛仔裤,上身的红色防风夹克袖管挽到了臂弯处。她的一头黑长发绑成了马尾,显得耳朵特别突出,就像是敞开的车门一般。随惠特里奇而来的那位年轻女子穿着一条宽松的海军蓝印花连衣裙,遮不住的起伏有致的身材似乎自玛丽莲·梦露后便不再流行了。她肤色白皙,双眼湛蓝,用一条海军蓝的丝带把自己咖啡色的头发绑成一束挂在脑后,仿佛耳际后开着一束鲜花。尽管身材有致、衣着光鲜,她的相貌却是平平。瓦斯克斯尽管穿得跟个男孩子似的,瘦得又像根竹竿,但她的黑眉毛和尖下巴衬得她的脸庞不只是好看,简直算得上美丽了。脸上淡掉的疤痕并不让她显得脆弱,反而更令她显得坚毅。那个年轻女子犹豫了一下,然后坐在了那张棕色的人造毛皮沙发上。
“韦茨人呢?”高大的男子环视了一圈办事处后问道。
“我想她是受够了,”格思里说道,“这位是蕾切尔·瓦斯克斯,我手下的新侦探。”
惠特里奇打量了一番这位波多黎各女孩,然后赏了她一个外交官式的笑容。“我想米歇尔应该会比我解释得更清楚。”他说道。
格思里点点头。
“你是个私家侦探,对吗?”那位年轻女子问道。
“算是吧。”格思里回答道。
米歇尔皱了皱眉头,咀嚼着他的话。她心里想着“算是吧”到底算不算正面回答时,她的面容生动了起来,突然让她显得不那么平庸了。“我需要你帮我找出到底是谁杀了我的堂妹,”她说道,“那帮警察以为他们确定了凶手,但他们错得一塌糊涂。”
瓦斯克斯电脑上的录像还在播放着,但她已经无心分神于此。她在用心地听着。她春天找到这份工作的时候,就盼着能遇上些性命攸关的案件。克莱顿·格思里尽管只是个私家侦探,但他却能打通关系违反法律,给一位十几岁的年轻人就配上一把手枪①,还给她办好了持枪证。工作的第一个月,她每天花六个小时在一个室内手枪练习场练习射击。小个子侦探在一旁喝着咖啡,帮她给弹匣填上子弹;他触动目标开关,大喊“开枪”,同时用秒表给她计时。瓦斯克斯每天都端着史密斯威森“长官专用”型手枪射击,累得两手手腕都酸了,就是因为格思里还教她换手射击。这一练习意味着她未来会碰上性命攸关的案子,就像格思里藏在底层抽屉里的左轮手枪所无言暗示的那样。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每天不是研究监视录像,就是坐在公园里或大街上监视着无所事事的行人。他们还会做点背景调查,也就是找到有关的人,问问他们是怎么看待他们的调查目标的。或者调查履历上的条目,搞清楚上面写的是不是真的人和真的公司,由此来判断他们有没有逃税,或者有没有犯罪记录。瓦斯克斯心想这大概也算是侦探的工作吧。也许人们靠这些营生也能过活。可当格思里把手枪递给她,跟她说“击中你的目标要像吐气一样容易”时,她指望做的可不是这种工作。而现在这两位拜访者,其中一位大声问出的问题已经足够抹消掉她的无聊,唤醒她的期待。
格思里回复给这位年轻的棕发女子一个吃惊的表情。他看了眼惠特里奇,然后问道:“你是指鲍曼谋杀案么?”
“没错!格雷格绝没可能杀了她,可警察却在昨晚把他逮捕了……”她说到这里话就断了,脸上凝着一团疑云。
在她提出第二个问题之前,格思里说道:“这是桩上流社会的谋杀案,这么说你也来自上流社会了。”侦探向惠特里奇投去怀疑的眼色。
“噢。我向哈里叔叔求助,他让我来找你。我猜你应该有点本事吧。”她又扫了格思里一眼,心里算着他到底值不值他预开的报价。
格思里点点头。“我听着呢,小姐,”他说道,“但我好奇你是不是不看报纸。这个因为鲍曼谋杀案而被逮捕的家伙,都不用我来指出,警察所有的证据都指向了他。”
“可他没犯事!”她坚称道。
卡米尔·鲍曼遇害的新闻已经在每座城市的头版头条登了一个礼拜了,近来遇害的人物里,她可算是新人一枚。她一头金发,美得摄人眼球,又是一个遇刺后遭到抛尸的年轻女子,还找不到任何重大的嫌犯。新闻记者们把这类案子叫作“芭比娃娃谋杀案”,因为死者都是貌美的女子。对于媒体来说,这类谋杀案简直就是一场嘉年华,潜逃的罪犯、性的意味、警匪大战,简直一应俱全。对于案件的最新发展,读者简直无所不知。
“我给那位小伙子指派了名律师。”惠特里奇主动说道。
“那位律师有没有门道?他手段怎么样?”
惠特里奇笑了。“恐怕那家律师事务所并不专精于刑事案件。这帮家伙通常对我都没什么用。然后警察找到了一把枪。”
“一把枪?”格思里一边在他的椅子里坐定,一边问道。
“看吧,你就觉得是他犯的事,”年轻女人说道,“警察也跟你错得一模一样!不是格雷格干的!他爱着她!”惠特里奇拍了拍她的肩膀,她才坐回到棕色的毛皮沙发上去。
银发男子的面容非常冷峻,看不出他到底在想什么。“你能接下这个案子么?”他问道。
格思里点点头,“我会从头调查到尾的。”
“谢谢。”惠特里奇说道。
瓦斯克斯走到窗前,看着第34街上的惠特里奇和他的侄女钻进了一辆配有司机的林肯城市汽车。这一次,街上并没有推着衣服架的孩子们挡道。林肯城市开走时,连喇叭轰鸣声都停歇了。“他到底是谁?”她问道。
“H. P. 惠特里奇,”格思里说道,“大名是哈里·佩恩·爱德华·惠特里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