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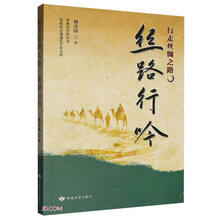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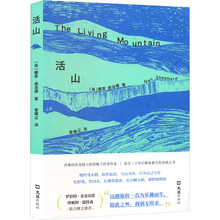



《徒步中国:用脚步丈量魅力中国》:
茫茫起点
湛蓝的天空下,我站在破烂的酒店外面,摸索着将4根绳子和登山扣系在帆布背包上。接着,我背上背包,拿起自己全新的越野行走杖,匆匆忙忙地戴上手套。空气中透着一股寒气,周边的世界一片寂静。迈出第一步时,绳子收紧,拴在身上的钢质拖车就开始跟在身后滚动起来,轮子开始吱吱作响。莫莉·布朗拖车上装着重100千克的露营装备、摄像设备、食物和水。拉动拖车的绳子就拴在我的腰上。我走下人行道,走到马路上,轮子就跟在我后面颠簸而行。
我打量了一下四周。我的探险伙伴兼摄影师利昂从我身边走过,他也背着背包,但没有带拖车。我们将轮流拉着莫莉走,先由我来拉。利昂右手举着一台摄像机。我让他在前面先走几米,然后停下来转身给我拍摄。接着我开始继续前行。
我们所在的地方名为赛音山达,是戈壁滩中部的一座蒙古国小城。这座小城是我们的起点,而我的家香港就在小城的南面,两者之间相隔3000英里。今天是旅程开始的第一天。
20世纪,蒙古国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都受到苏联的影响。同蒙古国多数城市一样,赛音山达也有着这个国家的种种印记。街道的两边排列着一板一眼的公寓楼。尽管它们被重新粉刷上了花哨的颜色,但整齐划一的窗户依然在那里,透露出一丝苦涩和冷漠。黑烟从一根巨大的灰色烟囱中飘出,飘散在干燥寒冷的空气中。建筑中间的土地都布满裂缝,里面全是褐色的戈壁滩尘土。我们仍然无法看到开阔的沙漠,因为赛音山达的四周被一座小型的山脊环绕,所以旅程的头一个小时里,我们的任务就是跨越这座小山。
许多蒙古人裹在厚厚的外套和围巾里面从我们身边走过,表情严肃。当看到我拉着莫莉时,他们皮肤粗糙的脸上露出笑容,也带着些许的困惑。从身边经过的汽车减慢了速度,司机和乘客们也盯着我们看。
我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好像脱离了这个世界。我难以相信我们终于动身了。我不知道前方等待自己的究竟是什么,不知道我们会看到什么地方,会遇到什么人,又会有什么样的探险。
遇到红灯时,我停了下来,和一排汽车一起等待着信号灯。两位中年妇女横过马路。在我盯着她们看时,她们咯咯地笑了起来,我害羞地回以笑容。我感觉自己就像是在表演拉马车的哑剧,而我自己就是那匹拉车的马。绿灯亮了,多数车都直行。利昂和我左转,再右转,出了城,走向苍茫茫的世界。
出城后依然是沥青路面,弯弯曲曲,一直延伸到山脚下。这条道路让人感到些许的压抑。我们走过城郊一些木棚和带围墙的房子。我开始迈开大步前行。
当我身子往前倾时,莫莉就会跟在身后往前滚动,每迈一步之前它又会往后退。靴子比较舒服,但感觉还不是很跟脚,但愿我已经适应了它们。头顶上是冷冷的太阳,唯一的声音就是莫莉的轮子持续发出的“咔咔”声,还有我的越野行走杖敲击沥青路面发出的“叮当”声。
随着上山的路越来越陡,我要费些力气才能拉动莫莉。寒冷刺骨的空气让人感觉呼吸都困难。现在只是11月14日,根本就算不上寒冬,可温度已经是零下10摄氏度了。与接下来的几个月相比,现在已经算是暖和的了。
利昂最初一直走在后面拍摄,现在已经赶了上来。几分钟后,我们来到了这座山的山口位置。我们两人停下脚步,远眺戈壁滩。眼前是大海般无边无际褐色的尘土和沙砾,在我们的四周蔓延开来。我只能看到在地平线上有隐隐约约的山脉,其余整个世界都是苍茫茫一片。
我摇摇头说:“老天,这真大呀。你觉得我们能走得出去吗?”“我们也许走得出去,现在我们就在这里了呀!”利昂操着一腔爱尔兰口音笑着回答说。他有着松软的棕发和年轻的脸庞,胡须刮得干干净净。25岁的他比我年轻9岁。他放下越野行走杖,架起三脚架。
我发现自己很难推算出这片土地到底有多大,我们又要用多长时间才能徒步穿越它。一周前,在搭乘飞机前往蒙古国首都乌兰巴托的途中,我曾经从飞机上俯瞰这块起起伏伏的平原,当时我估算我们会需要半天的时间才能走完飞机每分钟带我们飞过的路程。
不过,我看见前方并非完全空荡荡一片。沥青路面继续往西南方向延伸,只是我们要改变方向,朝东南方向行走,穿越这块平原。我拿起指南针,确认最明显的一条吉普车车辙印记大致朝向正确的方向。我也注意到在这条车辙印过去大概半英里的位置有一个白毛毡帐篷,也就是游牧民的蒙古包。它孤零零地竖立在茫茫戈壁滩上,就像是文明的最后一个岗哨。
利昂仍然趴在摄像机上。我一直等着他完成全景镜头的拍摄。
“可以走了吗?”我问道。
“我要再拍点儿东西,你先走。”一时四周万籁俱寂。这就是我们在茫茫平原上的起点线了。在数月忙乱的计划之后,没有什么再要说的,没有什么再要等待的,也没有什么再要准备的。
我深吸了一口气,身子往前倾,腰上依然绑着那根绳子。莫莉的轮子开始滚动起来。我们走下沥青路面,踏上褐色土地。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