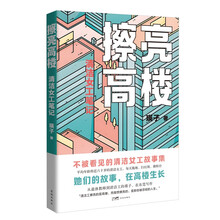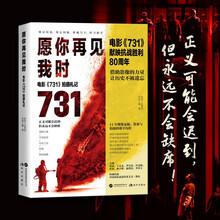《法兰西抵抗者》:
玛丽-弗朗索瓦兹·贝什泰尔(以下简称贝什泰尔):人们经常提这样的问题:你们是怎样成为抵抗者的?对你来说,那是怎么一回事呢?罗贝尔·尚贝隆(以下简称尚贝隆):确实,这是人们经常提出的一个问题。他们这样做是有理由的,因为引导每个法国男女参加抵抗运动的道路不一定都是相同的。
记得1939年底,法国的公众舆论对于国际形势演变的危险已经有了足够的注意,以至人们可以说,1939年9月3日,法国对希特勒的德国宣战并不是一场“晴天霹雳”。法国人备战已经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了。历史学家莫里斯·伏泰在谈到西班牙问题时曾经说过,西班牙内战是“在法国抵抗运动之前进行的一场抵抗斗争”,而今我基本上借用伏泰的这个观点。事实上,在许多法国民主人士、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缓慢前进的道路上,西班牙曾是某种决定性的因素……西班牙内战标志着一个决定性的历史转折。
贝什泰尔:这也是罗尔·唐居伊说过的话。
尚贝隆:因为正如我们后来将要看到的那样,法国抵抗运动的许多领导人大多是从国际纵队中发现的,特别是从法国纵队中发现的。
我们大致上可以说,对于许多抵抗者来说,参加抵抗斗争是不能脱离其家庭条件和社会环境的。我出身于一个左翼家庭。相比之下,我父亲的家族也许比我母亲的家族更左一些。我的曾祖父和曾祖母都属于巴黎地区这个深受让·饶勒斯或朱尔·盖德发表的声明影响的左翼组织。而我母亲那边,她的父母亲是布列塔尼人,即使他们属于人们所谓自由职业者的阶层,比如她的父亲是个医生,他们的身上也还保留着天主教的传统。这是一些长期参加支持政教分离的宣传运动的、开明的天主教徒。
我母亲是一个信徒,我的父亲则不信教,但他却不反对教会干预政治。反过来,我母亲却更加反对教权,因为她是在嬷嬷的修道院里长大的,并且从小就对修道院的生活留下了坏的记忆。不过,我母亲常去教堂点大蜡烛。这种做法比较简便,尤其是因为当年我们住在巴黎市政厅附近的圣热尔韦教堂旁边。可是,我们并不因此而信奉宗教文化。我们不到教堂去做弥撒。我们的住地有两个少年之家;一个是堂区的少年之家;另一个是公立学校的少年之家。为了伺机找些新会员来充实堂区的少年之家,本堂神甫来我们家登门拜访,对我母亲说:“夫人,您家里有几个孩子……但我们在教堂里却经常看不到他们的身影,这是多么遗憾啊!”我母亲就反驳神甫说:“我们不是一个信教者家庭。您要是离开我们的屋子,是会有好处的,否则,您就会有从窗户里出去的危险……”我父亲可以被划在不信教者之列,但即便这样,他也始终拒绝向反对教会干预政治的宗教游行提供任何支持,因为他认为,支持反教权游行是一个能损害整个工人阶级团结的政治错误,而丁人阶级有必要在争取权利和社会平等的斗争中,超越个人偏爱和实行团结。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