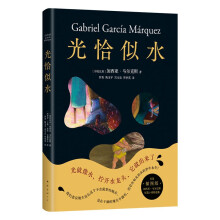这次他不会获胜。挑选他上场是个错误,维甘德的主意实在糟糕,因为他要想有获胜机会,跑完全程所需时间必须远远低于三十分钟;他必须达到他的原有纪录,但这一点他再也做不到了,再也做不到了。他是八名长跑运动员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他们正在起跑线上脱去运动衣,做决赛准备。他们慢慢地脱去运动衣衫;直到最后一刻,他们还想保持身体温暖,以便让肌肉处于松弛状态。这时,太阳露出脸来。雨后,阳光照在运动场上,炫人眼目;阳光底下,绿茵茵的草地闪闪发光;跑道上,一个个的小水坑闪烁着光芒。然而,风却未停止,这种变幻无常的狂风不断猛扑下来,无情地横扫看台,上午它就已经开始影响这场比赛……不会的,贝尔特这次绝对不会获胜,他连前三名也进入不了;脚脖子扭伤了的胡佩特甚至也比他有更多获胜的机会。然而,他们却让他替代胡佩特上场,随他去失败……他在草地上短跑似的跑几步,跑出去好长一截路;接着,他从肩部转动转动双臂,然后把手臂向前伸展伸展。
这时,他向我这儿,向看台这儿望望,不过并没有认出我来。他在寻找我吗?他盼望我站起身来,朝他挥挥手,好像告诉他没发生什么事吗?……一丝无可奈何的微笑浮现在他那疲惫不堪的脸上。他一只手理理稀疏的头发,让手停在后脑勺上,他的目光又在四处搜索看台。是啊,他老啦,参加这次长跑决赛他年龄太大啦;还没起跑,他就像个失败者的样子。但他不单单是无法赢得这场比赛,他将失去更多的东西。他们是最后一次让他出场,这一点他心里明白;他也知道,自己明年就是替补队员也甭想当了——让他去和体坛作最惨痛的告别吧…身着白色劳动罩衣的售货员——有的卖糖果,有的卖香肠,有的卖汽水——都站在过道上不动了。领位员走到木柱前,计时员在下面草地上举起手,示意已做好准备。比赛场上一片寂静,静得只能听到对面几面旗帜在风中发出哗啦啦的响声,没有任何别的寂静能像起跑前的这种寂静一样残酷无情了。这种极度紧张的、简直叫人窒息的寂静,不是别的什么,正是内心不安的最高表现——每次总归都是这样的。发令员喊参赛运动员各就各位,拉尔森这位发令员就要为这次万米赛跑发出起跑令。他个头矮小,身体胖墩墩的,穿着发令员惯穿的红色夹克衫,样子活像个小红萝卜。他身上没任何方面能让人看出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曾两次创世界赛跑纪录,而且在十八年前曾参加过某个著名的接力赛跑队。他蹒跚着来到起跑线后边,两只手各拿着把发令枪。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