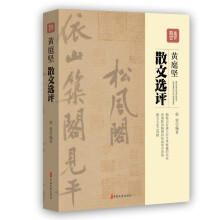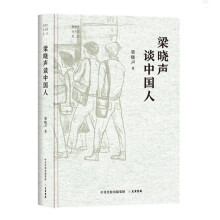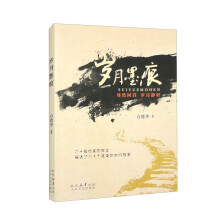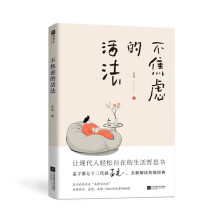我出生在纽约。我猜,你一定会说我是在纽约长大的。其实,我在那里只待到10岁,后来便搬到了康涅狄格(美国东北部的一个州——译者注)。
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坐在纽约公寓铺有地毯的地板上,翻阅着《国家地理》杂志。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对那些图片格外着迷,情不自禁地就想翻看它们。
最让我着迷的是那些放声大笑的孩童、头包印花手帕的妇女、以古银币点缀的部落头饰,以及在亚洲某山建在高桩上的岌岌可危的木屋。这些木屋隐藏在薄雾缭绕的山谷里,依山腰而建。不知为何,我竟对那些地方满怀憧憬,向往能够住在其中的一间房子里。
这些地方看起来十分遥远。有时,我能在下午五点由沃尔特·克朗凯特(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台柱——译者注)主播的晚间新闻里看见它们,在绿色贝雷帽巡查村落时看见它们,或是在沙沙作响的一个电影镜头中,拨开灌木丛看见它们。我不明白为什么这么多的士兵想炸掉建在高桩上的房屋,人们告诉我这是为了拯救那些裹着头帕的妇女和儿童。
从孩提时,我记得自己就流连于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在巨型恐龙骨骼、巨足以及熊和藏羚羊的标本面前感觉自身的藐小。我曾几个小时地盯着美洲印第安人长形的独木舟。那里还有身穿熊皮、头戴萨满面具的人物展,整座屋子都充斥着他们的力量。我可以连续几个小时地凝视这些萨满面具,想弄清它们到底像什么。
这家博物馆令我着迷。巨穴形的走廊通往一间屋子,那里摆设着许多身着爱斯基摩人、非洲人、阿拉伯人和波利尼西亚人传统服装的模特。年幼的我凝视着这些模特,很想知道真正身穿这些服饰的人们究竟是怎样生活的。后来有一天,博物馆开放了亚洲屋,于是我前去参观。
山地部落的影像又回来了:从无人攀登的群山中的融化冰川里流淌出一条河流,幽谷用这条河流切断层层梯田。我无法将它们从记忆中抹去。我再次想知道,在山腰上的木屋里居住会是什么情形。这样的木屋周围一无所有,除了风中摇曳的罂粟花和深谷中回荡的缥缈回声。我想要攀登那些群山。
后来,我搬到了康涅狄格州。
在高中时,我曾上过一堂有关印度和东南亚的课程。十分有趣的是,关于两个土地辽阔、人口众多、有千年历史的国家的内容被缩略为仅仅半学期的课程,而且是以“印度和东南亚”的科目教授美国高中生。这听起来有点像拉拉队长在足球场上讲的话。
他们忘记在课堂上告诉我们:这些强大的文化源于恒河、澜沧江和长江。它们汇集在无法攀登的神圣的西藏雪山前面。在听过几次讲座之后,我开始寻找旧的《国家地理》杂志。
我发现了它们,实际上我是在一本杂志里找到了一张地图。地图标示了位于东南亚大陆所有的山地部落,其中有越南、柬埔寨、缅甸、泰国和中国的云南省。以前,我从未听说过云南,它也没有出现在沃尔特·克朗凯特主播的新闻报道中。地图对苗族、傣族、彝族和长颈喀伦族进行了浪漫的描述。他们居住在建子高桩上的木屋里,皆裹着印花头帕。
我记得,我展开了这张旧地图,用胶带将它贴在我做作业的书桌上方的墙壁上。我告诉母亲我将记下所有这些部落的名称,我的确做到了。后来,我忘了那张地图,也忘了那些部落,我将它留在了早巳离开的那个儿时卧室的白灰墙上。
1981年,我作为留学生来到中国学习。当时,人人都穿蓝着绿。我没有看到在《国家地理》杂志上见过的那些色彩丰富的山地部落的装束,只看见在北京火车站游荡的目光阴郁的藏族人,还有许多坐在塞得满满的蓝绿色帆布包上的其他人。他们躺在布包上等购一张火车票,以返回离别不久且并不急于返回的地方。为什么他们都在等购车票呢?不久我便明白了,在当时即便是买一张火车票,你都要有关系才行。
1981年底,我离开了中国大陆前往香港。
那时的香港似乎是一切的中心。的确,它是中国商业的中心,而商业是生活的中心。每天,人们都在长时间地谈论生意。的确,我忘记了那些住在架在高桩上木屋里的山地部落。在合同谈判及讨价还价的刺耳声中,在开放的、发展的及处于困境的市场运作和币值跌升中,我渐渐淡忘了他们。在紧张的早间咖啡、午间茶及晚间的酒精中,我们探讨的话题全是关于市场。
20世纪80年代,我从事律师职业,为跨国公司来华投资草拟合同。我在香港的一家英国法律事务所工作。每天都身着黑色的西服,内穿带有白领和袖扣的蓝色衬衫。有时,我感觉自已已无法呼吸,仿佛被塞进了这套西服里,每天乘电梯上上下下,穿梭于楼层之间,就连晚上做梦都在影印文件。
这就是20世纪80年代一个专门研究中国贸易的律师在香港的生活。事实上,任何一个所谓的“中国通”都不能理解当时中国发生的一切。但那并不重要,没有人能理解。所以你可以非常从容地在中心金融区乘坐豪华办公大楼的电梯上上下下,谈论着实际上你并不理解的事情。对律师、会计、顾问和夜总会的女招待来说,讨论的事情都是按小时计账的,其价格与你微微点头、用双手递给潜在客户的名片上所印的真实身份相符。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