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衣无缝”坐落在离塞纳河不远的一条狭窄阴暗的街道上。丽塔屏住呼吸告诉我,那叫左岸咖啡馆,经常有现场表演。我们匆忙吃了晚餐,到时咖啡馆里已经有二十来人了,他们三三两两聚在一组镶在墙上的纯平电视屏幕前。这里看上去像个艺术品画廊,不过我拿起小册子时感觉起了变化。小册子用法语、英语和德语印刷。我直接翻到英文那页。
只读了几句,我就被雷得眉毛爬到了头顶。通篇都是洋溢着笨重狂热的宣言体,表达非常蹩脚,也许翻成德语能行。大意是要把艺术的前沿阵地拓展到新的感觉领域,填平被传统教条横亘在艺术和生活之间的鸿沟。尽管克里斯·波顿、鲁道夫·施瓦茨克格勒、大卫·聂鲁达等人已经做了一些开拓性工作,但现在到了把围墙推翻进入21 世纪的时候了。今夜,通过一个名为“詹妮弗的腿”的新作品,他们将做到这一点。
这话说得过于狂热和理想主义了,在我看来,这两者往往是一种危险的组合。
我觉得有点儿滑稽,“某人”也有同感,还不只一点点,他在德克斯特城堡的幽深地牢里发出咝咝的低笑。他就是黑夜行者,那快活劲儿总是能激发我的兴趣,让我精神振奋。我想,真的吗,黑夜行者会对一个“艺术”展览有兴趣?
我警觉地重新环顾展厅。屏幕四周,人们的低语不再像是出于对艺术的崇敬,直到这会儿我才发现这一片死寂中有种难以置信和震惊的味道。
我看看丽塔。她正皱着眉头读着小册子,还一边摇着头。“我听说过克里斯·波顿,他是美国人,”她说,“不过这个谁,施瓦茨克格勒?”她磕巴了一下,毕竟她一直花工夫研习的是法语,而不是德语。“哦,”她脸红了,“这上面说他切掉了自己的,呃……”她抬起头看看展厅里的人,他们都默默地看着屏幕上的内容。“哦,我的天。”她说。
“要不咱们走吧。”我说着,心底深处的朋友越发兴致勃勃了。
可丽塔已经走过去站在了第一个屏幕前,看清楚上面显示的内容后,她的嘴巴张得大大的,哆哆嗦嗦地像是要念一个很长很难的单词。“这是……这是……这是——”她说。
我飞快地瞥了屏幕一眼,丽塔又对了。
屏幕上是一段视频,一个年轻女子身着老式脱衣舞娘的装束,手上戴着手镯,后背装饰着羽毛。和这身性感服装所传达出来的含义相反的是,她一条腿放在桌子上,静止了十五秒之后,她搬起一个嗡嗡作响的桌锯放在大腿上,头向后一甩,嘴因为剧痛而大张。到此处,视频又跳回到开始部分,整个情景重复播放。
“我的天哪,”丽塔说道,然后摇摇头,“那是……那是特效。绝对是。”
我没这么肯定。首先,我已经得到黑夜行者的提示,这里正在发生一件很有意思的事儿。其次,那女人脸上的表情非常熟悉,很像我之前从事的艺术工作中常看到的那样。那种货真价实的痛苦,我相当肯定。难怪黑夜行者在咯咯窃笑。
我并不觉得好笑,假如这类艺术流行开了,我就得另外找乐子了。
不过这总算是一种有趣的纠结,我很愿意看看大庭广众之下别的视频都在演什么。但我似乎真的对丽塔负有某种责任,这些显然不是她看完以后还能保持脸不变色心不跳的东西。“好啦,”我说,“咱们去吃些甜点吧。”
她却只是摇着头重复说:“肯定是特效。”说完便挪到下一个屏幕前。
我跟着她走过去,另一段十五秒的视频中,年轻女人穿着一样的服饰。在这段视频里,她看上去正在从自己的大腿上切肉。她的表情已经变为一种麻木而持久的痛楚,好似痛得太久,她已经习惯了,但还是会觉得痛。奇怪的是,我曾在文斯·增冈在我“告别单身之夜”的聚会上播放的电影中看到过这表情,我记得那部片子叫《单身汉俱乐部》。女人低下头,注视着膝盖以下到胫骨六英寸的地方,那儿的肉被剥离,骨头露了出来。她脸上有一种表演成功的满意神情。
“哦,我的天。”丽塔喃喃着,然后挪向下一个屏幕。
我一直认为丽塔是个甜蜜愉快、乐观积极的女人,跟桑尼布鲁克农场的丽贝卡似的,路边的死猫都能引她落泪。可是此刻她却一步一步地浏览着显然大大超过她想象的可怕展览。她知道下一个视频会同样栩栩如生,不忍目睹。可她并不转身离去,而是静静地走向下一个屏幕。
更多观众进来了,每个人的脸上都慢慢浮现出震惊的表情。黑夜行者显然很欣赏这一切,可我开始觉得整件事儿有些无聊。我没法儿感受其中的意义,也没法儿从观众受罪的表情中找到什么乐子。说到底,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好吧,詹妮弗从自己的腿上切了些肉下来,可那又怎样?干吗要折磨自己呢?生活本身已经够折磨人的了。她想要证明什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丽塔似乎很想让自己再难受些,她残忍地从一个屏幕挪向另一个屏幕。我没办法,只得跟在她身后,绅士般地忍耐着她每次看到新的视频时发出的惊呼:“哦,天哪,哦,我的天哪。”
在房间远远的另一头,一大群人正看着墙上的什么东西,从我们这个角度只能看见金属框的边缘。他们脸上的表情都清楚地表明那是真正的好东西,是演出的精华部分,我有点儿忍不住想马上过去,然后好结束整件事情,可丽塔坚持按部就班地看下去,一个也不漏过。每一段视频都显示那女人在对她的腿进行可怕的操作。最后一个视频比别的稍微长一点儿,她正静静俯看着自己的腿,那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了,膝盖和踝骨之间除了一节光滑雪白的骨头,什么都没有;一段白骨的尽头是脚上完好无损的皮肉,看上去非常怪异。
更怪异的是詹妮弗脸上的表情。那是一种疲倦而又得胜的痛苦,好似她已经清楚地证明了一件事儿。我又看了一遍视频,还是没弄清楚她想证明什么。
丽塔似乎也没有头绪。她变得很沉默,只是看着最后一段视频,重复看了三遍,又摇了一次头,然后梦游般地朝那一大群注视着金属框的人飘过去。
事实证明,最后这一段才是整个展览中最有意思的部分。我听见黑夜行者在低笑着赞同。丽塔则破天荒地连“哦,我的天”也说不出来了。
一块正方形三合板上的金属框里,摆放的是詹妮弗的腿骨。膝盖以下的部分都在这里,如假包换。
“哦,”我说,“至少我们知道这不是特效了。”
“这是假的。”丽塔说,可我觉得连她自己也不信这话。
外面是一派太平盛世,阳光灿烂,远处传来教堂报时的钟声。可在这个小小的展馆内,此刻是一片暗淡,钟声听起来格外刺耳惊心,几乎遮住了我心里的另一个声响,那熟悉的咝咝声在提醒我更有趣的事儿还在后边。这声音几乎从未错过,于是我转过身来。
果然,展厅前方的人更多了。我看着大门打开,在一阵金属的嘁嘁喳喳声中,詹妮弗本人出现了。
之前的展厅已经很安静了,但和这会儿詹妮弗架着拐杖走进来的情形相比,简直像闹市狂欢。她面色苍白,憔悴不堪,脱衣舞服装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她缓慢而谨慎地走着,好像还不太适应拐杖。干净雪白的绑带缠在她那刚没了的断肢一端。
詹妮弗走近我们,我们正站在墙上的腿骨正面,我感觉丽塔朝后瑟缩着,想尽量离这个独腿女人远一点儿。我瞥了她一眼,她的脸差不多跟詹妮弗一样苍白,连气也喘不上来了。
我又回头去看。众人都跟丽塔一样,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詹妮弗,为她闪开一条通道。最终,她走到离她的腿骨一英尺远的地方,久久地凝视着,显然没意识到她让整个屋子的人都喘不上气了。然后,她身体前倾,从拐杖上抬起一只手,伸出去抚摩那节腿骨。
“真性感。”她说。
丽塔昏了过去。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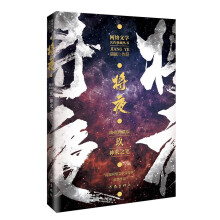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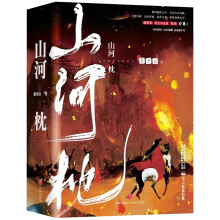


——《今日美国》
★一个游走于人间和地狱的判官,一个家人、朋友眼里的优秀拍档、合格伴侣,背地里却是杀人无数的双面人。我喜欢这个复杂、黑暗的连环杀手故事,更甚于《越狱》《迷失》《24小时》。
——《嗜血法医》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