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我回来的时候,那个货架旁边已经空无一人。我立刻推起购物车,俨然一个行色匆匆必须三下五除二干完家务事的职业女性。你一定想,你不就是这样一个角色吗?可是我很久没有这样看待自己了。我觉得,在那些排在我前面等待交款的人眼里,我这样不耐烦并非因为我是一名职业女性——她们帮助丈夫养家糊口,时间就是金钱——而是因为我更像一个逃犯,惶恐不安,恨不得马上溜走。
我把要买的那堆五颜六色的东西从购物车里取出来。鸡蛋盒子黏糊糊的,收银员打开查看。啊,玛丽·伍尔福德还是认出我了。
“十二个全破了!”那个姑娘惊讶地喊了起来,“我得让他们给您换一盒。”
我拦住了她。“不,不用了,”我说,“我着急走。就这样吧。”
“可是鸡蛋全都……”
“就这样吧!”在这个国家,要想让别人乖乖地听你的话,最好的办法莫过于让他们觉得你有点精神错乱。收银员用面巾纸擦了擦鸡蛋盒上的条形码,在机器上扫了一下,然后眼珠骨碌骨碌地转着,擦了擦手。
“哈查多琳,”我递上借记卡,收银员念着我的名字,声音很大,仿佛是说给排队人听的。快到傍晚了,正好是学生放学后打工的时间。这个姑娘大约十七岁,没准儿是凯文的同学呢。当然,这一带有好几所中学,她家兴许刚刚从加州搬来的呢。但是,看到她的眼神,我不再这么想。她直盯盯地看着我,“这个姓不常见呀。”
我不知道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不过这些事情真是让我烦透了。并非我没有羞耻之心,恰恰相反,我被所谓羞耻弄得筋疲力尽,浑身上下宛如沾满黏乎乎的鸡蛋清。这是一种无处宣泄的情感。“全纽约州姓哈查多琳的只有我一个,”我自我解嘲道,没好气地拿回借记卡。她把鸡蛋扔进一个塑料袋里,更多的蛋清流了出来。
我就这样回到了家——权且叫做家吧。你当然没有来过这里,那就让我给你描述一下吧。
你会大吃一惊。特别是当初我吵着闹着不想搬到郊区,如今却选择继续留在格拉德斯通。我是觉得应该住在离凯文不远、开车就能到的地方。除此而外,尽管我渴望没有人能认出我是谁,但并不是想让邻居们忘记我是怎样一个人。我求之不得,但是又有哪个城镇能够给我这样的机会呢?全世界只有这个地方能完完全全感觉到我生活中经历的所有变化。如今人们是否喜欢我远没有比是否理解我来得更重要。
付完律师费之后,剩下的钱虽然不多,但足够买一套小房子。只是租房子暂住在这里对我更为合适。我觉得,自个儿在这种积木玩具似的公寓套房生活,就像琴瑟和谐的婚姻,再合适不过了。噢,你恐怕要吓一跳,这些用很不结实的纤维板做成的家具是对你父亲的座右铭“材料决定一切”的公然挑衅。可我喜欢的恰恰是这种“靠不住”的感觉本身。
这里的一切都不牢固。通往二楼的楼梯陡峭,却没有扶手。我要是喝完三杯葡萄酒之后上楼睡觉,脚踩楼梯就会感到头晕目眩。地板吱吱作响,窗框走风漏气,整幢房子给人一种弱不经风、摇摇欲坠的感觉,仿佛整幢建筑就像设计极差的危楼般随时会轰然倒塌。楼下的卤素小灯泡用几个生了锈的衣架支撑着,连在天花板下的一根电线上,晃晃悠悠,忽明忽暗,为我的新生活平添了一种明灭不定的色彩。电话插座脱落,我与外部世界惟一的“联系”在两股焊接得十分糟糕的电线上不停地摇晃。晃来晃去,“联系”便常常被切断。房东倒是许诺给我换个好炉灶,可是对于我,换不换无所谓——炉灶上显示“开”的灯根本不亮。前门的把手经常一拧就掉,我只好再设法把它塞回去。但是那一截锁轴似乎在嘲弄我,或者说,像母亲一样在提醒我:不能离开这个家。
我还发现,这幢二层楼的“大方向”是把资源利用到极致。供暧不足,暖气片半死不活,散发出一点点热气。尽管还是十一月初,我已经把阀门开到最大了。冲澡的时候我只用热水,不兑凉水。而所谓热水的温度只不过让我不发抖而已。洗澡的时候,我惴惴不安,生怕热水马上用完。冰箱的刻度已经调到最大,可是牛奶只能保存三天。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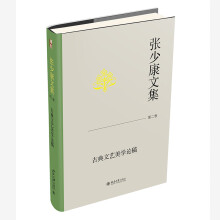
——《波士顿环球报》
一部挖掘到灵魂深处的女性力作。
——《纽约时报》
如此一部处处智慧、风格独特而又充满残忍的作品。
——《独立日报》
强有力度,弹眼落睛,能令人产生最深冥思的一部有关邪恶的作品。
——《出版家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