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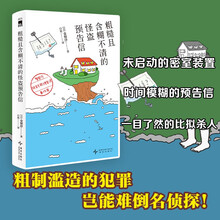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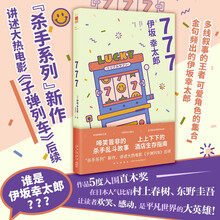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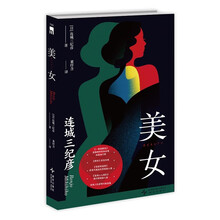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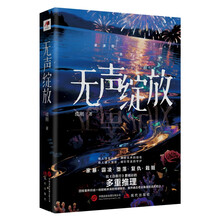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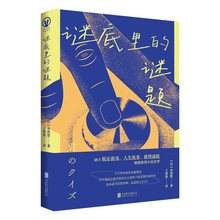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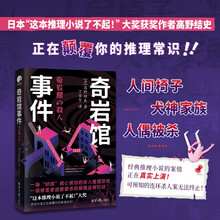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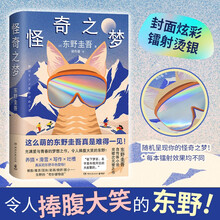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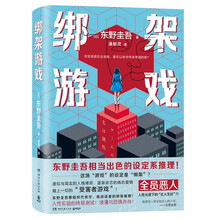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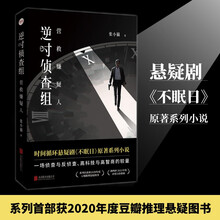
这可能是个恐怖故事。一个谋杀、侦探、黑色的恐怖故事。但实际上不是。
我,奥克西里奥,诗人,被誉为墨西哥诗坛之母。1967,或是1965,或是1962年从乌拉圭只身来到墨西哥,栖身于两位深孚众望的西班牙作家门下,甘心当他们的清洁女工,其中一位正是当年军队占领大学逮捕学生,我受困在哲学文学系女厕所时手边阅读的诗集的作者。可我也有自己的生活。我在那不勒斯区住过,在罗马区住过,在阿特诺尔·撒拉斯区住过。我的书籍丢了,衣服丢了。但不久后又有了别的图书,又有了别的衣裳。大学给我一些无关紧要的临时工作,后来又收了回去。
我很高,很瘦,金发,缺了几颗关键的牙齿,说话与笑时不得不捂住嘴巴,连接吻都感到难为情。我认识十七岁的阿图罗·贝拉诺,是他家人的朋友,与他经历过一次难忘的冒险……
整部作品洋溢着悲情感伤的氛围,展现出一幅拉美忧郁与暴力的历史图景,也是文艺个体在这种情境下所能做出的好回应。作家弗朗西斯科·高德曼认为《护身符》可以视作波拉尼奥特殊的自传,是他具有创造力和震撼力的作品之一。
《护身符》是罗贝托·波拉尼奥整个作品谱系中惟一出现“2666”字样的作品。
——《纽约时报》
★作为连接《荒野侦探》和《2666》的重要纽带,奥克西里奥所描述的那座被军队占领的大学成为拉美60和70年代的政治隐喻,更可说是一个时代的符号,那个无论是对文学还是生活的激情都仍然存在的时代。
——《波士顿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