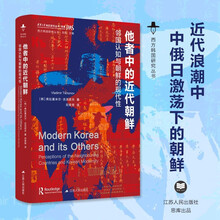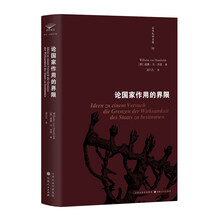押解人员引领战犯跨进管理所大门,迈上跃层“一”形台阶,通过长长的水泥地面走廊,“咣当”,沉重的铁门声,像一桶冰水从头到脚浇了他们一个透心凉。
“我手里有一张全体战犯的照片,那是他们刚刚被送到管理所时拍摄的,”日本《世界月刊》1998年5月号《坦白书是这样写出来的》一文的作者新井利男写道,“在这张照片上,有的人瞪着野兽般的眼睛,有的人强作微笑以掩饰内心的恐惧,有的人表现出一副绝望的神情,有的人脸上刻着西伯利亚饱受饥饿和残酷劳动折磨的印迹,每一个人在精神上都有些异常。”在内心里,他们充满恐惧。西伯利亚的饥饿与强劳动没有压垮他们的身体,没有泯灭他们的精神幻想。因为苏联法律取消了死刑,最多科刑二十五年,何况他们身上还没有背负“战犯”的罪名。如今,管理所大门牌子上把“战犯”帽子加身,又落在了“仇国仇人”手里,怎能不叫人心悬半空?等候在两侧并排的一个个大大小小的监房门前,又一次点名开始了。
969人,一一回应,对号人室,分别走进各自分住的5栋监舍。每间监舍,正门挂着一把铁锁,门扇上方为哨兵留有一个等人高的窥视方孔。舍内水泥走道两旁,是高约40厘米的木板通铺,每间监舍10个人左右,分住两侧。
天亮了,中国管理所第一夜过去了。像货车换客车、黑面包换白面包一样,新的环境、新的幻想搅拌着新的不安,喜忧交织的情绪持续了一夜。一宿醒来炸了“庙”,不是因为住房等级划分,而是因为住户身份认定。墙上一纸写着活动时间表和注意事项的公示单,“战犯管理所”的落款让战犯们像看到了生死牌那样的恐惧。
“‘战犯’,多么恨人的字眼!一世英名岂容玷辱?满身的血液直冲头顶。”“战犯管理所”的牌子刺痛着战犯们的视觉。《战犯管理条例》让他们了解了“管理所”不同于苏联羁押地的功能。“‘战犯’是审判问题,‘战俘’是遣返问题,前者有可能上断头台,后者才会生还而兑现那位苏联看守所长许诺的‘达冒伊’(俄语‘回家’)。”一字之差,生死之别,岂能含混!睁眼的闭目沉默,闭眼的瞪大了两眼;起床的躺下去,卧铺的爬了起来;“唧唧喳喳”的哑了嘴巴,没说话的“嘟嘟哝哝”……他们骚动起来,狂怒起来,歇斯底里起来。
有人把它撕下来,恨不能捏成粉末,踏上两只脚;有人把它贴了回去,担心过分闹大,惹来杀身之祸。
一个叫:“什么,我们是战犯吗?不是,不是!”十个喊:“我们是战俘,不是战犯,统统的不是!”百个吼:“巴嘎牙鲁!‘战犯’?岂有此理,绝对不接受!”管理所以监舍床位为序,给他们身上挂上了20厘米长条的号码牌,并拍了单人半身面部相片:中将师团长藤田茂的代号为937,中将师团长佐佐真之助为927,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为924,伪满洲国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为933,伪满洲国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为932……号码代替姓名,就像烙印一样抹不掉了,更加忍无可忍。一名师团长发出最后通牒:“我和我的部下不是战犯,而是战俘,”“必须无条件释放!”每一张表情不一的脸上,都泛着无奈、不安、愤怒、辩解、绝望的旋涡。一些人则大发雷霆,把淤积脑中5年的不满、怨恨和愤懑,一股脑儿地发泄出来:“在苏联当俘虏就够窝囊的了,眼下我们怎么一夜之间成了真正的战犯了?”“你们最大的官是校官,怎能管得了我们,有什么资格采问我?”“我吃够了监狱的饭,拉出去枪毙算了!”“等着瞧,你们(指有进步表现的同类)这些大和民族的叛徒!”更有甚者,连“战俘”也不认同,说什么:“我们厌恶听到‘俘虏’这个词。我们不认为自己是俘虏的,我们是根据(天皇)《诏书》停止军事行动的,我们从来没有遭到过失败。如果战争继续下去的话,我们所有的军人都会战死在沙场上。根据以上陈述,我请求严重注意‘俘虏’一词的使用。”“是不是俘虏,是不是战犯,你们会慢慢地明白的,”看守员听不懂日本话,不知所以;管教人员听明白了,不卑不亢、不冷不热地说,“大家长途跋涉,想必是大大的累了,还是安静地休息去吧,冷静下来自己想一想,会慢慢地弄清楚的,会统统地明白。”朦胧不清如坠云雾的谈话,叫人满腹狐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看来,也只好这样了,慢慢地走着瞧吧!”他们一些人只能无可奈何。
战犯,战俘?按照他们的设想,宁可作为战俘暂留活命于敌手,也不要作为战犯未卜游魂回日本,这是不是有违于他们的初衷,不够一个彻底的天皇忠臣、“武士道”的勇士呢?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