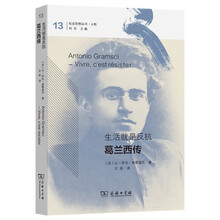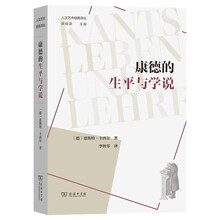《罗素传:疯狂的幽灵(1921—1970)》:
第一章 堕落天使:49岁时的罗素“我的脑子现在不如从前。我已经过了最佳年龄,因此现在自然受人赞美了。”接近50岁生日那段时间,这是罗素常常挂在嘴上的那种诙谐的自谦之辞。1921年12月3日,他出席了在剑桥大学求学时认识的老友(这时已是事业有成的富裕律师)查尔斯·桑格在切尔西举行的宴会,对坐在身旁的弗吉尼亚·伍尔夫说了上面这一番话。置身于这样的朋友中间,罗素不禁深刻地意识到这个事实:30年前,他和桑格一起学习数学;与那时相比,他已经变了许多。弗吉尼亚·伍尔夫语气温和,一直在旁边催促(伍尔夫当天夜里在日记中写道,“伯迪是热情的自我主义者,这一点起到积极作用”),于是他开始反思出现在他身上的这些变化。他告诉她,他依然认为,数学是“最高贵的艺术形式”,然而它不是他本人希望重新从事的那种艺术了:“人50岁时大脑变得呆板;再过一两个月,我就50岁了。”(实际上,他次年5月才满50岁)他说,他可以撰写更多哲学著作,但是“我得挣钱”,于是从那以后,他的大多数著述都是有人付费的报刊文章。他从事严肃思想研究的日子已经结束了。他告诉伍尔夫,在28至38岁之间,他“生活在地窖里,每天工作”,那时“激情控制了我”。如今,他已经接受了自己的状态,“我不再期望任何新的情感体验。我觉得,当我遇到一个新人时,已经不会发生什么浪漫的事情了”。
弗吉尼亚·伍尔夫在她的日记中如实记录了这些话语,既没有做出任何评价,也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但是,罗素的其他朋友沮丧地发现,罗素出现了这些变化。两个月之后,韦布在位于格罗夫纳路的寓所中举行宴会。在比阿特丽斯·韦布的笔下,罗素“玩世不恭,说话诙谐,思维敏捷”,然而“不能与自己或者他人和平相处”。从政治角度看,她倾向于将他视为轻量级人物:“他态度从来都不严肃,他的经济和政治观点和他性情一样,随着个人的好恶波动……他过去懒散,没有耐心,不能通过深思熟虑的社会行动,解决让自由最大化的问题。”她认为,他总的说来已经沉沦了:如今,他扮演着堕落天使的角色,不乏靡菲斯特的诙谐,具有很好的分析头脑,常常嘲笑他人。这些因素让他成为给人刺激的同伴。但是,我带着悲伤,回顾对这位老友的看法。他作为文人,可能取得成功;但是,我怀疑,他是否可以成为有价值的思想家?我相当确定,他将不会获得爱情带来的幸福,不会进入创造性工作带来的平和心境。我回想20年之前的情景,伯迪·罗素专注思考抽象问题,散发着阳刚之气,做事显示出骑士风度,而且不乏同志情谊,亲切幽默,令人愉快,显示出完美的个人尊严,而且还带着一点清教主义的意味。对比之下,我看到他现在的状态,不禁感到悲伤:他不修边幅,身体不佳,玩世不恭,未老先衰,与……一个举止轻浮、信奉实利主义哲学的女子在一起。况且,他并不而且无法尊重她。
比阿特丽斯·韦布一直以敏锐的目光,记录罗素的个性变化,然而以上描绘的用词特别尖锐,在某种程度上有所歪曲。其原因也许在于,她与罗素的第一任妻子艾丽丝保持着忠诚的朋友关系,对他的第二任妻子朵拉持排斥态度(“一个其貌不扬的矮子”)——朵拉27岁,年龄只有艾丽丝的一半,但是比较显老,不能被称为“姑娘”。
在以上日记中,弗吉尼亚·伍尔夫和比阿特丽斯·韦布对罗素进行了简短的描述,特别突出的一点是他给老友们的感觉:在1921年,他们必须做出努力,才能理解罗素在人生和个性上出现的变化。1914年世界大战爆发以来,罗素经历了许多事情,疏远了他的朋友们;战争结束之后,他很长时间身在国外,先是在苏联,后来在中国。现在,他娶了新妻子,回到他们之中,从事的新职业是记者兼演说家,在人生的若干基本方面有了新的态度。鉴于这些原因,他看来肯定需要与朋友共度许多时间,一方面反思这些变化,另一方面试图解释,他们在19世纪90年代认识的那个伯特兰·罗素——那个态度认真、自命不凡、主要爱好是沉思逻辑学和数学领域中的抽象真理的年轻人——后来的人生经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