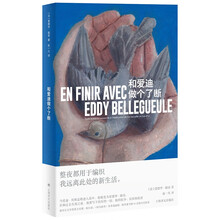我是个卖肉的。一个人的两只手做什么最能体现他的价值?所以在告诉别人名字之前,我总是先告诉他我是干什么的。杰克?满?司徒是我买来的名字。这是我赖以谋生的名字。旧金山是我入境的港口。船进港的时候,金门大桥看着很宽,但船开到桥底下的时候,它的影子又窄得惊人。我听着桥上来往的车辆呼啸而过。船靠岸时我感觉到海水在推着船向前走,我渴望着能开始新的人生里程。
我能读得懂肉。我的手指像秃鹰的尖嘴一样在大理石般的肉面上滑动,从腱子里翻出肌肉,凭感觉找出那块金贵的软腰窝。我把刀尖对准血管的一头,一刀插进去,然后像扯粗绳子一样把血管猛地一下拽出来。我用刀刃沿着骨头划下去,这样肉就像木兰花的花瓣一样剥落下来。
我是个高手。我的拇指和手掌能把肉抓得很紧,手眼准得能劈裂一声哨音。我熟悉肉里面闻起来像金属味那样的腐
烂味。我肩扛着冰冷的肉块奔跑,在重压之下直喘粗气。我明白妥协是种颜色,是种突然出现的气味,一种明确的付出。白天,我感觉就像有根锯条在我的关节上来回拉扯;晚上,它在我的前臂上嗡嗡作响。作为一个屠夫,我想要控制好刀的力度和方向,想一下子就把骨头砍断;但作为一个人,我只想跟肉上的记号说话。如果我不能说话算话,我就不会把话说出来去烦别人。没人乐意去揣测别人没说出来的想法。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