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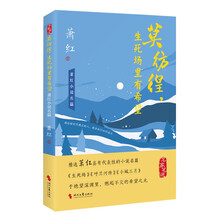

一部客观冷静地思索国家、个人现状及未来的佳作;
对历史人物设身处地的理解,对历史事件跳出时空局限的客观评判;
不随大流,有主见,引导读者独立思考,了解今天、知晓未来。
《知识分子丛书:趣味高于一切》是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谢泳的随笔集,作者在本书中谈现代学术的规范,谈学术批评的正确态度,谈新旧交替时期人心的嬗变;谈20世纪三四十年代大学的学风,谈学者之间交往和思想的比较,谈自由主义思想在20世纪中国的影响;谈自己对好书奇文的欣赏,谈自己嗜书成癖的学生……在书中,作者怀着真正的“同情”,带领我们与一个个有名的或无名的历史人物进行着跨越时空的对话,进入一个个虽然时隔不久、但却正被遗忘的历史事件之中。
胡适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湖北程朝富先生有一天给我打电话,问我记不记得胡适在哪里说过“历史是个小姑娘,可以任人打扮”这样的话,我一时还真没有想起来,他说要问一下耿云志先生。上世纪50年代批判胡适的时候,这句话流行极广,可谓妇孺皆知。尽管引用者多数按自己的记忆来复述这句话,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但大体是这个意思。程先生为什么要问我这句话的出处,我没有再细问,事情也就过去了。
前不久我看《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北京大学图书馆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6月),因为边看边查书,就又想起了这件事。北京大学图书馆编辑的这部书,可以说是近年胡适研究中的一个大收获,因为披露了许多新材料。胡适留在大陆的遗物本来在一处(东厂胡同一号),50年代批判胡适的时候,当时科学院的近代史所调看过一部分,侯外庐《揭露美帝国主义奴才胡适的反动面貌》一文中,就使用过这些材料。后来其中的善本书到了北图,还有一部分留给了后来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前几年耿云志先生编辑《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主要是东厂胡同的材料,北大这部分就没有收进去,这部分中数量较大的是胡适的英文往来书信。因为查阅时翻了一些关于胡适的书,就又想到了程先生前次提到的问题。
首先,我要说,胡适从来就没有说过那样的话。那句话是由另外的话变化过来的,而且与胡适的原意恰好相反。50年代批判胡适的时候。好多人并不是不知道这句话的原意,但多数作了故意的曲解,如李达、孙定国等人的批判文章中。这句话出自胡适的名文《实验主义》,是胡适当时的一个长篇演讲稿,最初发表在《新青年》上。是胡适介绍詹姆士的实在论哲学思想时说的。原话是:“实在是我们自己改造过的实在。这个实在里面含有无数人造的分子。实在是一个狠服从的女孩子,他百依百顺的由我们替他涂抹起来,装扮起来。实好比一块大理石到了我们手里,由我们雕成什么像。”(《胡适作品集》,第四集,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86年10月)胡适在文章的前面本来已经讲清楚了对实在的理解,他这里只是用了一个比喻的说法。胡适说,所谓实在含有三大部分。一是感觉;二是感觉与感觉之间及意象与意象之间的种种关系;三是旧有的真理。可以看出来胡适原话是讲哲学的,与历史毫无关系。但这句话在很长时间内却变成了胡适评价历史的一个基本态度。好多人写文章一上来就是胡适说过,“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其实,胡适是很实事求是的人,他对历史的态度非常认真,最提倡说话要有证据。他怎么会说出那样的话呢?但在批判运动中,人们是不敢也不愿意去搞清真实情况的。这句话是如何流传开来的,一时不好查考,但可能与冯友兰当时的一篇文章有关。
冯友兰在批判胡适运动中写了《哲学史与政治——论胡适哲学史工作和他底反动的政治路线的关系》。其中有一段说:“实用主义者的胡适,本来认为历史是可以随便摆弄的。历史像个‘千依百顺的女孩子’,是可以随便装扮涂抹的。”(《胡适思想批判》,第六集,81页,三联书店,1955年8月)
当时对许多普通人来说,他们了解胡适,不是通过阅读胡适的著作(那时胡适的著作已不可能公开出版了)。他们只能通过那些批判胡适的文章来认识胡适,所以一个历史人物的形象就改变了。顺便说一句,就在这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胡适未刊书信日记》中还收有一封1934年6月20日冯友兰给胡适的信,信写得极为客气,对胡适充满敬意。
金岳霖的理想和无奈
西南联大的教授中,冯友兰和金岳霖的人生道路都很漫长,经历了许多历史变幻。冯友兰的命运,给中国知识分子留下许多启示,这人们已经说得很多了。我曾写过一篇《晚年冯友兰》,说了我对他的理解。我对冯先生的学问是门外汉,我感兴趣的是他的经历。我想从他的经历中看一代知识分子的坎坷人生。我常常想这样一个问题:在同样的历史条件下,同样面临不适应,这时决定一个知识分子选择的动力是什么?过去的理想、文化的传统能起多大作用?也许这是难以说清楚的。但有一点,我觉得可以说,也容易找到相应的历史事实,那就是一个人的个性。个性这东西,有时候和信仰和传统是分裂的。在环境压力下的知识分子,信仰和传统的力量有时会很快消失,生存的力量是决定性的。像冯友兰在“文革”中的转变,从他早年的行为中也能找到相应的依据。台湾马逢华曾说过当年他和萧公权闲聊,说起清华旧事,萧公权说,战前清华园教授同仁之间就流行这样的说法:
WhateverDaisenSays,itgoes;
Whateveritgoes,ChisenSays。
这话的意思是岱孙怎么说,事情就怎么做;事情怎么做,芝生就怎么说(马逢华《记西南联大的几位教授》,《传记文学》,52卷6期)。虽是学林掌故,但我们却能从细微处见到一个知识分子的个性。面临同样的历史巨变,冯友兰和金岳霖的转变有点类似。1974年冯友兰在《光明日报》发表《咏史二十五首(并序)》,这些诗明显留有当时的历史痕迹。《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初稿》中有“金岳霖来信称赞《咏史诗》”的记载(蔡仲德编,《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初稿》,524页,河南人民出版社),可见金岳霖当时的思想状况。
金岳霖的道路,和他同时代的著名学者一样,都是早年清华,然后留美,回国做大学教授,虽然专业不同,但他们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整体教育背景决定了他们对政治的态度,这个态度简单说就是“参政意识”。金岳霖的专业懂得的人不多,他当年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已是首屈一指的人物,1948年他曾和冯友兰一起当选为中央研究院人文组的院士,它是当时一个学者的最高荣誉。金岳霖曾说过他一生对政治不感兴趣,但对政治不感兴趣,不等于对政治没有见解。过去的知识分子,多数对政治是不感兴趣的,但同时他们又都对政治保持有热情,金岳霖曾在许多公开发表的宣言中签过名,对学生运动,他也和多数大学教授一样,有自己一贯的看法。
金岳霖早年在西南联大的学生殷海光曾这样描述当年金岳霖对他的影响:“在这样的氛围里,我忽然碰见业师金岳霖先生。真像浓雾里看见太阳!这对我一辈子在思想上的影响太具决定作用了。他不仅是一位教逻辑和英国经验论的教授,并且是一位道德感极强烈的知识分子。昆明七年教诲,严峻的论断,以及道德意识的呼唤,现在回想起来实在铸造了我的性格和思想生命。……论他本人,他是那么质实、谨严、和易、幽默、格调高,从来不拿恭维话送人情,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155页,上海远东出版社)
一个教授当年的风范给学生留下如此深刻的印象,可以想见金岳霖的精神魅力。但同样一个金岳霖,在后来却突然发生了变化。他的学生王浩曾说,金先生的绝大部分文章和3本专著都完成于1948年底以前。“金先生于1949年以前及以后追求了两个很不相同的理想。”对此王浩的评价是“所以一个人如果多年来专心追求一个理想而中途忽然转向另一个理想,恐怕不易得到像持续一个理想所能得到的成绩”。(《金岳霖学术思想研究》,4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他先后参与了对杜威、胡适和罗素的批判,参与了对梁漱溟、费孝通、章伯钧的批判。这个被他的学生认为“在是非真妄之际一点也不含糊”的人,突然转变了。他的转变是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普遍选择,人们对他的选择也许已不再苛求,但如何评价这种选择,从这种选择中能看出什么东西,却是不容含糊的。王中江在《理性与浪漫——金岳霖的生活及其哲学》中有一段话说得极好。他说:“对他50年代以前的哲学的片面的批判和否定,使我感到愤怒和痛苦。对此,金到底是如何感受的,我们已不能详细得知了,但我忍受不了。从理智上,我同情他,一心想为他的所为作出辩护,把他个人的悲剧性失误,转换成同时代的悲剧性曲折;但是,从感情上,我不能原谅他,我甚至反感,我要求他对他自己的失误承担责任。”(见该书255页,河南人民出版社)金岳霖这一代知识分子,本来言论应该是最具独立性的,但在历史巨变中,我们没有看见这种独立性。金岳霖晚年,对自己的选择有很沉痛的反思,但他的话说得很含蓄。他说:“在新中国成立前,我没有搞过什么政治,那时我似乎有自知之明。我在新中国成立后是不是失去了这个自知之明呢?新中国成立后,绝大多数的人都心明眼亮起来了,难道我反而糊涂了?我也没有变成糊涂人。事实是既有政治,也是‘政治’。”(刘培育编,《金岳霖的回忆与回忆金岳霖》,60页,四川教育出版社)金岳霖其实在这里想要说的是,多数人放弃了独立性,我也就不再坚持了。为什么要这样呢?金岳霖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花大功夫,长时间,学习政治,端正政治态度。我这样的人有条件争取入盟入党,难道我可以不争取吗?不错,我是一个搞抽象思维的人,但是,我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这一点如果我不承认,怎么说得上有自知之明呢?根据这一点我就争取入盟入党了。”(同上)
1957年,金岳霖平安无事,不知这是否和他与毛主席吃过4次饭有关,但与金岳霖主动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而尽可能迎合时代有关。关于金岳霖早年的生活,我们现在知道的不多,知道的也多是关于他个人生活的一些趣闻,如他和林徽因一家的关系之类。我读过一些国内出版的关于金岳霖的书,感到金岳霖这样的知识分子是读书人的楷模,身上有许多优秀的品质,学问好,人又高雅,有中国人的机智(如他有作联语的嗜好),又有西方人的幽默。从他晚年的谈话中,能感到他在做出违心之论时,是有过考虑的,不过他“终究是一个活的、具体的人”。就个性而言,金岳霖大概属于比较软弱的人。
储安平与季羡林
2009年7月4号,我在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主持了一个纪念储安平诞辰一百周年的学术会议。会议结束不久,就传来了季羡林去世的消息,许多报纸、杂志要我就此谈谈自己的感想,我都推辞了。倒不是自己无话可说,而是感觉世道日薄,在历史选择中,我们为什么总是对那些真正给历史留下记忆的东西不加珍惜,而对俗世的荣光倒很看重。我想起了储安平和季羡林。
季羡林是1911年生人,比储安平小两岁。上世纪40年代中期,储安平在上海办《观察》时,季羡林是封面底下列名的78位“撰稿人”之一,给《观察》写过一些文章,其中有一篇《论现行的留学政策》,是批评当时政府留学政策的,这样的文章,季羡林后来就没再写过。《观察》1950年复刊时,季羡林写过一篇《把学术还给人民大众》,是在新时潮影响下写的。
季羡林与储安平是老朋友。上世纪30年代中期,储安平编过一本名为《文学时代》的文艺月刊,当时季羡林正准备去德国留学,后来给这本刊物写了《表的喜剧》。储安平发表这篇文章时,将季羡林写给他的两封信,也在“编辑后记”中发表了,当时季羡林已在德国。储安平说:“我们得恳切地感谢季羡林先生的盛意,他在那样遥远的地方,竟然没有忘了我们这一个稚嫩的刊物,我们在筹备本刊出版的时候,正是他在筹备去国外的时候……他临走时候说,他到了德国,第一篇文章就给我们,我们真得敬佩这样一位守诺的朋友。”
季羡林的这两封信是很好的散文,可惜由于是夹在“编辑后记”中发表的,很少为人注意。文中有两句话给我印象极深:“俄国人民是好人民个个都有朝气。政府却是个怪政府……使你没有自由。”我在1998年出版《逝去的年代》的时候,其中有一篇小文章,曾谈到过季羡林的这个经历。季羡林后来与储安平的关系,我不很清楚,但想到知识分子在时代转移之际的选择,还是很有感慨。陈寅恪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表达过,易代之际知识分子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他认为“其贤者拙者,常感受痛苦,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储安平就是一个拙者,但也是一个贤者,我认为历史更应该纪念的是他。我们不好判断季羡林1949年后的顺应时代,是不是完全发自知内心,但他选择了完全认同这个时代的主流价值却是一个基本事实。1955年底,中共中央统战部为了配合将要召开的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搞了好几个调查报告,其中对北京大学的调查主要在文、史、哲三系,当时统战部按自己对新旧知识分子的理解分类,把季羡林划分在进步知识分子一类中,报告里有这样的话:“受旧社会影响较小,解放后接受新事物较快,政治思想进步较大。这种人约有五四人,以季羡林为代表。季羡林在抗战胜利后不久回国,解放前对现实略有不满。解放后当选北大工会文教部长,积极工作,努力学习政治理论及时事政策,参加抗美援朝运动等工作。通过这一系列现实的教育和他自己的努力,政治上进步较显著。”(中共中央办公厅机要室印发,《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参考资料(第二辑)》48页)在同一个调查报告中,钱钟书被划在“反动的”知识分子一类里。
……
知识分子丛书总序/李银河
第一辑 书生私见
当明引不当暗袭
陈寅恪谈学术规范
如何理解档案解密
学术批评要与人为善
知青的最后辉煌
“五四周期率”与社会进步
今天我们如何了解国史
历史教员的责任
我们有没有自由主义传统?
关于燕京大学研究院
危机时代中的西南联大
老北大和老清华的外聘教授
恢复高考与阶层流动
张芝联译《英国大学》
第二辑 斯人斯事
胡适与冯友兰
胡适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胡适的直觉
胡适关心黄晖
金岳霖的理想和无奈
张东荪这个人
再说张东荪
范文澜的无奈
吴恩裕的学术转向
吴世昌的选择
周一良五十年代的思想倾向
想起杨人楩先生
怎样理解舒芜
储安平《给弟弟们的信》
储安平死因小考
储安平与季羡林
二钱与陈衍之关系
钱锺书的“代笔”之作
钱锺书的科举观
第三辑 趣味至上
仪式出于内心
培养学生的趣味
毕业后如何读书
《遗珠》好
方便面源于厦门
关于洋装书
爱读书的林建刚
书中的文章不是写出来的,更不是逼出来的,而是“流”出来的。因为心里太满,冲动太强,所以不得不“流”出来的。相信读者会从作品的字里行间看到作者写作时内心的快乐,这将是一位读者所能祈望得到的极致。
——李银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