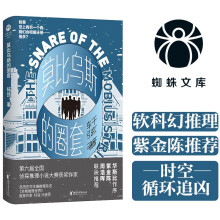虽然残雪不怎么用本身表明了主观感觉的形容词和动词,例如害怕和焦虑等,一种强烈的、主观主义情感的印象还是传达给读者了。这是通过客观的描叙来表达的,如以上提到的那些。这种描叙可以被解释成内在意象的客观化投影,或象征的时空具体化。这种对客观的运用,远不是为了增强我们的现实感觉,反而有唤起一种妄想狂感觉的效果,这种妄想感觉嵌在原文的风景里。
因此,这个故事可以从几个层次上来阅读。从表面层次看来,它说到一个中了魔的人,被阴险的“亲戚们”打扰和迫害,她企图通过做梦来走出噩梦般的“现实”。但与此同时,描叙语气的特殊的主观性似乎让人觉得可以有种不同的阅读,似乎让读者产生一种怀疑,觉得这个故事也可能是描写一种内在的妄想狂的病例,可能亲戚们事实上只不过是一般的、无恶意的人,进出这所房子,因为很普通的理由在种一棵树,而远方的送葬者只不过是一些在山坡上散步的人们,由于“我”的妄想狂的凝视而转化成了具有威胁性的主观的幻象。我们从前面分析中得知,她是在河边疯走的时候被亲戚们发现的,然后被他们捆起来,放到了一个破庙里面。这对于猜疑的、“追求正常的”(意义建造的)读者来说。也可以意味着将一个精神分裂的人强迫送到医院去治疗。他们也声称曾经救过她的命,那以后她给自己做了一个猴子的假面,这表明她是作为治愈者或正常人来行动的(假如我们遵循这种解释线索的话),因为在前面写到了亲戚们像猴子一样跳跃。这两种阅读都意味了一种强烈的对抗——一方是亲戚(或外界),另一方是“我”——在善与恶或理智与疯狂之间建立了清晰的界限。
然而,一种更深入的阅读展现了二者之间的同谋甚至同一性。亲戚们实际上也是妄想狂的、多疑的,他们谈到长年的恐怖和监视:“莫非有人偷听?到处都是贼,什么事都不可靠,我们不要忽视这类问题。从刮大风的那天起,天上就出现了裂缝……”文本中确实带来了两种极端的、分开的剧情说明,而“我”在那之间浮动:一种是耀眼的、平和的永恒,一种是泥泞的、忧心忡忡的现在。由于“我”在第一个世界里是一个局外人,在第二个世界里就成了风景的一部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