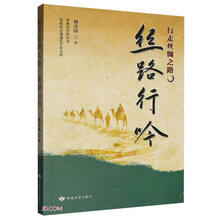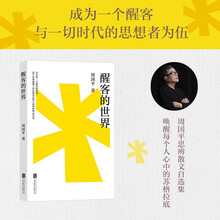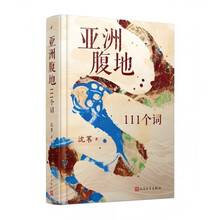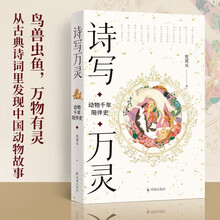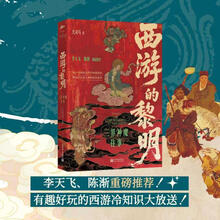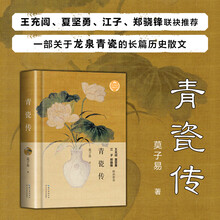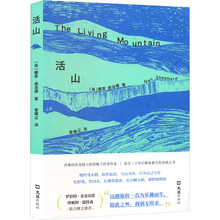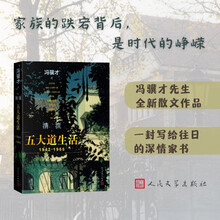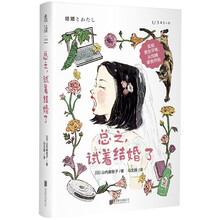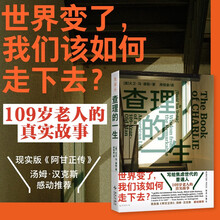像我们这样的三口之家,吃饭是很随意的。
尤其是午餐。
有段时间专攻馒头。下班的路上顺便买了,回家烧一锅汤,内容是肉片虾仁鸭蛋粉丝青菜西红柿等等。一边喝着汤,一边啃又白又胖的馒头,佐菜是报纸和书和笑话,算很惬意的。
直到有一天,我女儿照着镜子问:“妈妈,我快变成馒头了没有?”
才紧急刹车。
改吃面条。
还是刚才的汤水还是刚才的内容,只是把一小把粉丝换成一大束阳春面,由共同拥有的一盘过渡到每人一碗,如此,天天泡制,吃到各位家长严重感到面条快从鼻孔里游出来了,才打住。
于是上街去吃。
鱼丸店、汤圆店、面线店、炒粉店一溜地依街而设,这便是我们的好去处。
去的更频繁些的,是一家小面店。算一算,吃龄有四五年了。
混得很熟。他们称我先生“叔叔”,称我则“阿姨”,而我的小女儿,则成了他们宠爱的孩子。
每次都逗着她玩,要收她当小徒弟啦,手把手教她包小笼包包煎包啦,听她小嘴嘟嘟讲我们学校怎么怎么啦,任她在小面店跑来窜去淘气。要是久些没去,路过他们的店,总有人赶出来问:“逸舟,怎么好久不见?”
有一次我忘了带钱包,要往回家拿,他们坚决不肯,说什么时候给都可以。
有一次碰到个卖菜刀的,非卖我不可。他们说:她都不煮饭,买什么菜刀?算了算了,我们买吧。
有一次在这个小面店我认识了一位后来成为我朋友的台湾人,同样的闽南乡音,同样是姓吕的,同样有个蓓蕾一般的小女儿,谈得很投机呵!分别时,我和他都争着替对方付账,小面店收他的不收我的。偏心。
有一次我和先生中午都有公务应酬,把小女儿的午餐托给小面店,他们连连说:“放心放心,保证逸舟到晚上肚子还是圆滚滚的。”
有一次我先生出差,小女儿回爷爷家度暑假了。我生了一场急病,单位的女友来照顾我。到了吃饭时间,我让她们到小面店填肚子。两个女家伙喝面汤喝得醉醉地提出来:“我们是欧逸舟的妈妈的好朋友,她病在床上,能不能借个杯子给带点回去?”居然也成了。
有一次小面店只有小徒弟在,我问他:“你不是本地人?”
“四川人。”
“一个月工资多少?”
“起先一百二十元,后来一百五十元,现在一百八十元。”
“够不够花销?”
“够了。我都寄回去。我早上五点钟起床发面团,干到晚上十点才关门,累得要命,要什么花销。”
“有没有到隔壁去消费?”隔壁是间关门关窗的发廊。老板也在小面店吃包饭。一个盛夏的傍晚,忽然停电,从发廊里涌出几位妙龄女郎,散发出浓浓的风尘味道。才恍然大悟,这发廊究竟是什么的干活。人也真微妙,再见到老板,打招呼就显得勉强了,渐渐连点头也省略了。但总存着好奇心。
“哪里敢?!”小徒弟说,“一个月工资还不够人家开销一次。”
“这么贵呀?”
“半小时叫一钟。客人要交老板三十元,另外得给小姐小费。”
“小费怎么给法?”
“五十元、一百元凭客人高兴。有一位小姐是我老乡,有一次碰到个大方的客人,打开腰包叫她自己拿,她胆子很小,才拿了三张,三百元。等于我两个月的工资。”
我大笑起来,我说:“她们会坐班房的。”
小徒弟反驳我:“什么呀,抓了总要放。我那位老乡也被抓过,写信叫老板去保她。”
我又一次大笑:“我前几天骑车一路数过去,咱们××路有×家发廊。”
所以会心血来潮去数天上有多少星星,地上有多少发廊,是因为我女儿留了一条极美丽的长辫子,出生以来就没剪过。却不幸在学校染上虱子,找了几家发廊,都不给剪,说是弄不来小孩的头。原来,她们是为大人服务的。
小徒弟听了“哇”了一声。“我们那里十乡八里才一两个剃头师傅。我本来要学理发,我妈不让,说长头发又不是长庄稼,哪里有那么多头剃呀!好后悔好后悔!”
没等我开口,我女儿赶紧帮助教育他:“叔叔,你不要后悔,开发廊有什么好!都是搞按摩。按摩要用手,手又没消毒,很不卫生。”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