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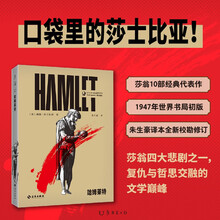






《世界文学名著典藏:美丽与哀愁·蒲公英》是川端康成晚期的作品,1961年1月,《世界文学名著典藏:美丽与哀愁·蒲公英》开始在日本《妇人公论》杂志上连载,直至1963年10月结束。川端康成通过细腻真实的对话,把故事经过和人物形象完整地展现给读者,对人物却没有偏袒或鞭挞,久野的犹疑,母亲的躲避,他都不加评论,只是和盘托出,把审判的权利交给读者,让读者的感情随着小说人物的脉搏起伏跳动。
在东海道线“鸽”号特快列车的嘹望车厢里,车窗下并排五把转椅,其中外端的一把随着列车的晃动而静静地自动旋转。大木年雄见到了,久久地注视着。大木在这里坐着的低矮的扶手椅是固定的,当然不能转动。
陈望车厢里只有大木一人。大木深深靠在扶手椅上,望着那把旋转的转椅。那把转椅并不是按一定的方向和一定的速度旋转,而是时快时慢,时而停转,有时还反转。大木在车厢里独自一人望着一把转椅自动旋转,诱发起大木心中的寂寞,引发起种种遐思。
这一天是年末的二十九日。大木到京都去听除夕的钟声。
大木在除夕之夜用收音机听除夕钟声的习惯已经连续几年了呢?这一节目是几年前开办的呢?自从这一节目开办以来,不是每次都听吗?日本各地的古寺名钟鸣响时,还配以播音员的解说。在这一节目里,播音员的播音由于辞旧迎新而带有华美兼咏叹的声调。那节奏缓慢的古寺钟声的余韵,让人感到时光的流逝,古老日本的空寂苍凉。北国寺院的钟声鸣响之后,便是九州的钟声,而每年除夕都是以京都各寺院的钟声结束。京都寺院很多,有时收音机会收到若干寺院钟声的交相鸣响。
在播放除夕钟声的时候,妻子、女儿或在厨房操办年饭,或整理物品,或选配和服,或插花,仍在不停地劳作,而大木却总是坐在茶室里收听收音机的。
随着除夕的钟声,大木不由回顾过去的一年。他感慨横生。其感慨因年而异,有时激奋,有时凄苦,有时陷入悔恨和悲伤之中。即使有时厌烦播音员感伤的语言和声音,但钟声却震撼着大木的心。而且,他早就有一种心愿:何时能够不通过收音机,而是在岁暮的京都直接听一听各古老寺院的除夕钟声。就是在这一年的岁暮,他忽然打定主意,前往京都。他还涌动着一种不可告人的心思,要去见住在京都阔别多年的上野音子,并同她一起聆听除夕的钟声。音子移居京都以后,与大木几乎断绝音讯,只知道她似乎作为日本画家目前已白成一家,至今仍过着独身生活。
由于前往京都是突然生起的念头,而且大木也不是事先定好日期、买好“特快”车票那种性格的人,所以他没有快车票,便在横滨站搭乘了“鸽”号嘹望车厢。他想,临近岁暮,东海道线也许很拥挤,但乘坐嘹望车厢,老勤杂工是熟人,也许能想法给找个坐位吧。
“鸽”号午后从东京、横滨发车,傍晚到达京都,从大阪、京都返回也是午后发车,爱睡早觉的大木感到舒服,所以往返京都总是乘坐“鸽”号。二等车 (分为一等、二等、三等的二等车)的列车员小姐们一般都认识大木。
一上车,没想到二等车很空。年末的二十九日也许乘客还不多,三十日、三十一日大概要拥挤了吧。
大木望着那一把旋转的转椅,不由陷人关于“命运” 的深深思考。这时,老勤杂工给大木送来了煎茶。
“就我一个人?”大木说。
“噢,有五六位。” “元旦车挤吗?” “不挤,元旦车很空。您元旦回来吗?” “是的。元旦不回来的话……” “我给您联系好,元旦我不执勤……” “拜托了。” 老勤杂工走后,大木环视四周,见车厢尽头的扶手椅的下面放着两个白色皮革的提包。那是稍稍有些薄的四方型新式提包。白色的皮革衬以斑驳的淡茶色,是日本所少见的上等品。椅子的上面还放着一个豹皮大型女用手提包。这些东西的主人大概是美I~IJk 吧。他们好像是到餐车去了。
窗外温暖浓重的烟霭中,杂木林向后流逝。烟霭上空遥远的白云中透出微光。那光好像是从地面照射上去似的。但是,随着列车的奔驰,天晴了起来。车窗的阳光投射到地板深处。列车从松山脚下奔驰,地上落满了松针。一丛竹叶黄了。闪光的波浪拍击着黑色的岬角。
从餐车回来的两对美国中年夫妇,当车过沼津见到富土山时,便站在窗前频频拍照。然而过了一会儿,当富士山完全显现在原野上的时候,他们好像拍累了似的,反而把身子转了回来。
冬天昼短,大木目送着一条浓重的银灰色的河流,抬起头,正与落日相对。少顷,从黑云的弓形罅隙里冷冷地透出白色的余辉,许久没有消逝。在早已亮灯的车厢里,不知什么力的作用,转椅一齐转了半圈。但是,一直不停转动的,仍然仅仅是外端的那把转椅。
大木一到京都,就去了京都饭店。大木想,音子也许会来饭店的,所以希望住一个安静些的房间。电梯似乎已经到了六七层,但这个饭店是依傍东山的陡坡建起来的,因而沿着长长的走廊往里走,走到尽头还是一楼。走廊旁边的各个房间相当安静,大概都没有住人吧。但是,到了十点多钟,两侧的房间突然喧嚣起外国人的声音。大木问了一下值班的男仆。
“是两家,两家共计十二个孩子。”男仆回答道。十二个孩子不仅在房间大声说话,而且在两家的房间窜来窜去,在走廊乱跑乱跳。明明空着许多房间,可为什么把大木的房间夹在中间,让这么吵闹的客人住在两侧呢?但是大木想,都是些孩子,过一会儿就会睡的。可这些孩子也许是由于外出旅行而兴奋的缘故吧,总也静不下来。尤其是孩子在走廊乱跑的脚步声更为刺耳。大木从床上起来了。
这时,两侧房间的外国话的喧噪反而使大木感到孤独。“鸽”号嘹望车厢中那把独自旋转的转椅又浮现脑际,大木感到孤独在自己心中无声地旋转。
大木在重新考虑,为了听除夕的钟声和与上野音子相见而来到京都,然而见音子和听钟声,到底哪个是主要目的,哪个是顺便的呢?能听到除夕的钟声是确定无疑的,但能否见到音子却有些茫然。那确定无疑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个口实,而那茫然的东西不正是心底深处的愿望吗?大木是打算和音子一起聆听除夕的钟声而来京都的。临来时,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大木和音子之间已经长年隔绝。尽管现在音子似乎仍过着独身生活,但能否肯与昔日的情人相会,能否被约出来,这对大木来说的确是不得而知的。
“不,她现在……”大木嘟哝了一句,但‘她” 有了怎样的变化,大木对她的现在并不了然。
音子该是借住寺院的配院,同女弟子一起生活的。大木在一家美术杂志见过照片,那个配院并不是只有一、两间屋子,而是很像一户人家,用作画室的房间似乎也很宽敞。院落也很幽雅。这幅照片,虽然是音子正在执笔作画的姿势,略低着头,但是从额头到鼻梁完全看得出的确是她。她并未因中年而发福,显得文雅而端庄。这幅照片使大木展望未来比回忆过去所受到的谴责更为强烈——正是自己从这位女性的生涯中夺走了其成为妻子、成为母亲的权利。当然,在见到这本杂志的人们中,产生这种感觉的只有大木一人而已。与音子没有多大关系的人们,只是把音子看作是一位移居京都的具有京都风韵的美貌女画家罢了。
二十九日夜里就这样吧。大木打算在第二天三十日给音子打个电话,或者到音子家中拜访。但是,早上被外国孩子吵醒起床后,又有些胆怯而犹豫不定。
还是先寄一封快信吧。他坐在桌前,但一开头便又不知如何下笔才好。大木看着房间备置的便笺仍是一张白纸,又想,也可以不见音子,自己一个人听过除夕的钟声后便回去。
大木很早就被两侧房间的孩子们吵醒,但当那两家外国人走后,便又重新入睡了。起床时,已经将近十一点了。P2-5 ,哪个是顺便的呢?能听到除夕的钟声是确定无疑的,但能否见到音子却有些茫然。那确定无疑的东西只不过是一个口实,而那茫然的东西不正是心底深处的愿望吗?大木是打算和音子一起聆听除夕的钟声而来京都的。临来时,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难事。
但是,大木和音子之间已经长年隔绝。尽管现在音子似乎仍过着独身生活,但能否肯与昔日的情人相会,能否被约出来,这对大木来说的确是不得而知的。
“不,她现在……”大木嘟哝了一句,但‘她” 有了怎样的变化,大木对她的现在并不了然。
音子该是借住寺院的配院,同女弟子一起生活的。大木在一家美术杂志见过照片,那个配院并不是只有一、两间屋子,而是很像一户人家,用作画室的房间似乎也很宽敞。院落也很幽雅。这幅照片,虽然是音子正在执笔作画的姿势,略低着头,但是从额头到鼻梁完全看得出的确是她。她并未因中年而发福,显得文雅而端庄。
这幅照片使大木展望未来比回忆过去所受到的谴责更为强烈—— 正是自己从这位女性的生涯中夺走了其成为妻子、成为母亲的权利。当然,在见到这本杂志的人们中,产生这种感觉的只有大木一人而已。与音子没有多大关系的人们,只是把音子看作是一位移居京都的具有京都风韵的美貌女画家罢了。
二十九日夜里就这样吧。大木打算在第二天三十日给音子打个电话,或者到音子家中拜访。但是,早上被外国孩子吵醒起床后,又有些胆怯而犹豫不定。还是先寄一封快信吧。他坐在桌前,但一开头便又不知如何下笔才好。大木看着房间备置的便笺仍是一张白纸,又想,也可以不见音子,自己一个人听过除夕的钟声后便回去。
大木很早就被两侧房间的孩子们吵醒,但当那两家外国人走后,便又重新入睡了。起床时,已经将近十一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