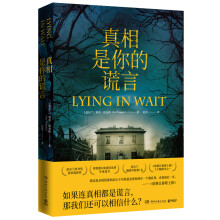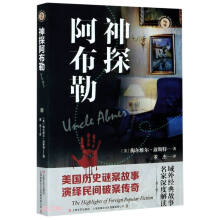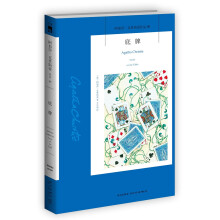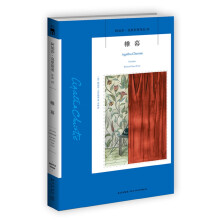吕雉很早就进入了刘邦的生活,早到公元前214年。
比这一年更早的时候,刘邦无所事事,终日闲荡于沛县街市,优哉游哉,漫不经心,把周遭一切都看在眼里,又都没放在眼里。
街市逢集,来了不少挑担背筐的外乡人,遭遇亲友,连声招呼寒暄,笑烂了一张脸。拉拉扯扯去往狗肉摊,称上二斤狗肉,用荷叶包了,一同进到酒铺中,买些散酒,把狗肉铺在桌上,纷纷落座,吱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肉,边吃边侃,慢腾腾地,直到散了集才分手。
狗肉混杂老酒的醇香,飘进刘邦鼻腔,挥之不去。
与他同行者,还有二^、——发小卢绾、好友周勃。
前日,周勃给人当出殡鼓手,得了些碎银,刚够买壶酒。有酒无菜,好比聋子看戏,净瞧眼前热闹,品不出更多滋味。
刘邦说:“无妨,有酒便好,狗肉算我的。”其实他兜里并无一文钱,只将卢、周二人带往樊哙的狗肉摊。
首次在樊哙那里赊账,刘邦心里还打鼓。赊得多了,习以为常,便不再有心理负担。
赊账,无疑是一项磨炼心理素质的经济活动。
樊屠夫也豪爽,从不记账,哪笔账清了,哪笔账没还,心头没数。
一路行来,刘邦眼前已浮出樊哙屠狗的情景——一条狗夹在他两腿之间,动弹不得,他提刀便剜,只消几刀,便如剥花生壳般利索,将狗皮剥落下来拎在手上。裸狗眼眶盈满惶恐热泪,战栗哀号,继而呜咽几声,倒地而亡。
每看到此处,刘邦都忍不住击掌喝个彩。
今日,又能观赏樊哙的劲爆表演了。
三人加快脚步,到了地方,一看,空无一人——樊哙没出摊儿。
“咋办?”周勃问。
“喝寡酒也可。”卢绾道。
“不。”刘邦一挥手,“换地儿。”三人又辗转前往刘邦大哥家蹭饭,倒霉透顶的一天,就这样开始了。
刘邦的大哥刘伯,是个本分人、规矩人。其人生轨迹,乃千人一面之钟点人生:按点长大,按点干活,按点娶亲,按点产子,循规蹈矩,传宗接代,周而复始,宛如当了一辈子钟点工。
刘伯明白到什么年龄该干什么,却从没想过自己爱干什么。
刘邦明白自己爱干什么,却从没想过到什么年龄该干什么。
刘伯很满意自己的小日子,锅里有饭菜,床上有女人。
平常人,你还想要什么呢?他想,刘邦理应羡慕他,理应像他一样,踏实一些,勤劳一些。
刘邦心领神会,极勤劳地来蹭饭,回回都吃得很踏实。
今日,偕友人前来,刘伯出外干活,单剩大嫂独自在家。
见到刘邦,大嫂只用鼻子发声:“哼!”“啥意思?”周勃问。
“打招呼。”刘邦答。
卢绾深知底细,只顾偷笑。
说话间,饭点儿己到,却不见大嫂生火造饭。
刘邦进厨房踅摸,只见清锅冷灶,转而问:“吃什么?”“吃屁!”大嫂摔盆砸碗敲锅铲。
“也行。”刘邦踌躇半秒,又问,“可否给碗凉水冲服?”大嫂用足以击落苍蝇的目光盯他一眼,眼中的内容是给他的评价:混吃等死。
外屋,卢绾和周勃已经笑抽了。
“走!”刘邦掩饰难堪,尽量潇洒地一挥手。
凉水都混不到一碗,刘邦无语,喝了几口周勃的酒,心中发闷,身子打晃,晃晃悠悠回到家。父亲见他这副尊容,止不住感叹:“浪荡啊浪荡。”继而絮叨:“小时候叫你念书,你光捣蛋;长大了,有手有脚却不干活,混至今日,你脚下的地在走,你身边的水在流,你是一无所有。”往常,絮叨到此为止。今日奇了,刘太公越说越来劲:“似你这般不成器,往后只怕连婆娘都讨不到,去给人家做赘婿算了。”此言犹如尖刀,在刘邦心上划了一道。
秦时,赘婿等同贱民。始皇修长城,征发的对象便包括贱民、罪犯和赘婿。
刘邦再无所谓,父亲这句骂词也不免让他怒火中烧。
他愤然出了家门,并不知往哪儿去。漫无目的地走街串巷,迎面撞上一帮人,为首是一壮汉,名唤雍齿,乃沛县名流。全称:沛县著名流氓。打瞎子、骂聋子、酗酒滋事,无恶不为。
刘邦曾与此人有些过节,今日狭路相逢,雍齿岂能放过。
刘邦环顾左右,此时想跑,已无退路。一帮小流氓早将他围堵,这打是挨定了。
刘邦准备捂脸,无论受多大伤,面子要保住。
一场狂殴即将来临,王陵钻了出来。此人与刘邦有些交情,在雍齿跟前也说得上话。
刘邦一直称他为大哥。今日,这大哥上帝般降临,救他于危难。
雍齿却不依不饶,一腔到手猎物被人夺走的悲愤。
王陵深知黑道含义。所谓黑道,就是为面子而活的一条道。吃了对方的亏,必然要喊一句:这事儿若传出去,我以后还怎么混!若要雍齿这般轻易放过刘邦,以后他还怎么混?王陵有心让刘邦摆桌酒席,大家一醉化积怨。
主意虽好,刘邦犯难,他身无分文,如何摆席?王陵一眼瞧出刘邦的窘迫,却不点破,只若无其事道:“二位给我一分薄面,同饮几盏,如何?”酒桌之上,男人通常比平时豪爽、通达,大话、义气话喷涌而出。刘邦只觉自己在演戏,他向雍齿敬的酒,分明是赔罪酒。敬得憋屈,喝得窝心。冷酒下了肚,混合着窝心的火,憋屈的酸,硬生生如长矛顶在胃里,难受得想吐,却吐不出来。
这一日,本该快活的。哪知赊肉未遂,转而蹭饭却遭受冷脸,回家又被阿父责骂,愤然出走,竟遇仇家。
回想起来,这般倒霉的日子,只是无数个倒霉日子的缩影。所谓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殊不知好运与厄运,相生相克,此消彼长。如老子言: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在这倒霉透顶的一天行将过去之时,否极泰来了。
刘邦走出酒馆,别了王陵、雍齿等人,臊眉搭眼地行于街市。忽而有人从背后拍肩:“嘿,你好难找!”转过头看,一中年男子立于面前,面矜持有儒者风。
“萧何兄。”“县衙招吏,特意告知。”萧何抱怨道,“四处寻不见你,你倒逍遥,在此喝大酒。”刘邦尴尬讪笑。君只见我孟浪喝酒,却不知那酒几乎烧烂我的自尊。
这倒霉的一日,因了萧何传达的消息,别开洞天,柳暗花明。
夜深人静,刘邦双手枕于脑后,仰躺思索:秋来冬去,自己在这世上,已苟活三十五载,究竟想要什么?一个濒临中年的男人,如何才能活出些气魄来?他想到自己的偶像信陵君。此君乃魏昭王之子,堂下门客三千,汇聚三教九流。其壮观景象可想而知,以至于当时各诸侯国内,只知魏国有个信陵君,不知有个魏安釐王。
信陵君威望浩荡,使各诸侯国十余年不敢向魏国用兵。
刘邦何尝不想成为这等酷男。无奈家境贫瘠,与信陵君那样的富二代完全不在一个起跑点上。
再一想,纵然富贵又怎样?沛县不乏富家子弟,不照样被雍齿一类的流氓肆意欺凌么?再观信陵君,风光半生,最终被魏王剥了兵权,只好沉湎于酒色,聊以解愁,愁也没解掉,最终卒于酒色。倘若他当了魏王,大权在握,也许不会如此颓丧,也许他的人生会是另一番景象。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