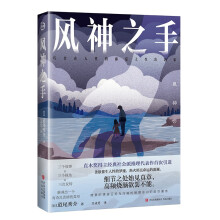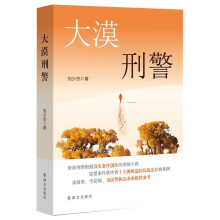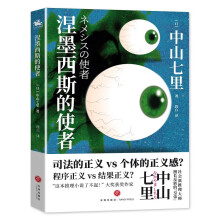这年春天,我十五岁了。谁料刚过完生日,左侧的肺就发生了破裂。
那正是我离开东京住到夜见山市外祖父母家后的第三天。本来次日要去转学的新学校报到上课——无奈偏偏就在那天夜里发生了这档子事儿。
一九九八年四月二十日。
那个星期一本应是我第一天去新学校上课的日子,结果却变成了我人生中第二次人院。上一次发生在半年前,也同样由于左侧肺部的破裂。
“医生说,这次入院要住上个十天八天了。”
面对刚入院不久、独自躺在病床上忍受着持续胸痛和呼吸困难的我,一大早赶来医院探望的外祖母民江如是说道。
“医生还说,你的病虽然不至于动手术,但下午需要插根管子做个治疗。”
“啊……去年也做过。”
“像这种治疗做多了,会不会变成惯性啊。——怎么样?还觉得闷吗,恒一?”
“嗯……闷。”
其实和几小时前坐救护车来医院时的剧烈疼痛及胸闷相比,静躺了一段时间之后,人确实一点一点地轻松起来,可即便如此,也着实难熬。那张显示半边肺部凹瘪变形的X光片在我脑中时隐时现,挥之不去。
“也真是,才来这里就……唉。”
“……对不起啊,外婆。”
“说什么呢!你可别往心里去,生病也是没办法的事。”
外祖母微笑地注视着我,眼角皱纹倍增。虽说今年已有六十三岁了,身子仍不失硬朗,对我也爱护有加。不过两人像现在这般近距离说话,似乎还是头一回。
“那……怜子阿姨呢?上班没迟到吧?”
“不用担心,那孩子一向规规矩矩的。这不,她中间回来过一趟,然后又在平常的时间出门了。”
“替我转告她,说给她添麻烦了……”
昨日深夜,一阵似曾相识的异样感觉突然袭来:肺部深处犹如漏了气般躁动不安,特殊的剧痛伴随着呼吸困难。“莫非又犯了?”当时陷于半恐慌状态急于求救的我向客厅里的怜子阿姨求助。
怜子阿姨比我已过世的母亲小十一岁。了解情况后,她马上叫了救护车,还陪我一同去医院。
谢谢你,怜子阿姨!
很抱歉,真的。
本想当面说声感谢,无奈当时状况严重,没法子感谢。加上我向来不擅长和她面对面地交谈……或许不是不擅长,而是过于紧张吧。
“我还带了些替换的衣服来。有什么需要,尽管说。”
“——谢谢。”
看着外祖母将一个大大的手提袋放在床沿上,我用沙哑的声音道了谢。考虑到一不小心又会使得疼痛加剧,我不得不保持头部靠在枕上的姿势,只是略微点了点下巴。
“外婆,那个——我爸爸他……”
“还没跟他说呢。阳介现在不是在印度吗,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才能联系上他。今晚我就让怜子……”
“不用,还是我……自己来联系。手机……我忘在房里了……只要拿来就行。”
“哦,是吗。”
父亲名叫榊原阳介,就职于东京某著名大学,从事文化人类学或社会生态学的研究。身为一名研究者,四十出头就当上教授或许称得上优秀,可作为一位父亲是否称职,就不得不打上问号了。
说来说去,皆因他长期漂泊在外。
因为需要实地考察,父亲常常奔波于国内外,却将独子抛在家中不顾。拜父亲所赐,我自小学时起便拥有了一份特殊的自信:若论家务本领,绝不输给班上的任何人。
上周,父亲仓促决定去了印度。听说要留在当地开展近一年的调查研究活动。我这次突然寄宿到夜见山市的外祖父母家,很大程度上正因为这事。
“恒一啊,你和你爸的关系还好吧?”
“嗯,还行。”我回答道。尽管心中对父亲有些许不满,但还不至于讨厌他。
“话说回来啊,阳介也是个重情重义的人哪,”外祖母自言自语道,“理津子死后都过了这么多年,也不见他再成个家,还不时地来帮助我们……”
理津子是我母亲,和父亲阳介年纪相差十岁。十五年前——即生我的那一年,年仅二十六岁的母亲就早早地离开了人世。
从父亲的一位老友口中得知,父亲还在大学当讲师时就与身为学生的母亲相识并相恋了。“当时他出手可快了!”那位朋友来家中时,借着酒兴,狠狠把父亲调侃了一番。
母亲死后至今,父亲身边倒也不乏追求者。虽然这话由儿子来说有些欠妥,不过父亲确实是位优秀的研究工作者,以五十一岁的年龄来说,显得年轻英俊、温和大方,既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又有相当的经济实力,再加上单身一人,又怎会不被人追?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