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争论以及更多的问题都会让大脑不得消停。他看不到前景,她得不出生活的普遍意义。她的情绪说变就变,他则一到下午就精疲力竭。她指责她父亲“将家园变卖给了鸡蛋场”。他母亲一人在哈德洼过日子,他本想把她接入他们的教师之家,可实际上他又在找管理优良的老人院,因为他要“理智处理”这个问题。她,理论上原本很想要一个孩子,但自从地理课上的印度次大陆成了她的心病,她从此就自觉放弃了做母亲的可能。对他来说,学校里的孩子已经让他够受的了,到了周末他更见不得孩子,可最近他又说:“咱们这套老式单元房,加上花园,住三个人肯定没问题,就算是母亲搬来居住。”
这些思虑让他们很不轻松。孩子总是一个问题。不论他们在伊策霍“荷尔斯泰因购物中心”采购,还是在布罗克多夫附近的易北河岸边参加反核电站的抗议活动;不论在考虑买双人床垫,还是在买二手车时,孩子问题都会浮现出来。眼睛总要瞄向小孩用品,暗暗希望排卵那刻会受孕,购车时会查看车门有没有防范小孩手动的保险机制。交谈中说的都是如果这样,如果那样,比如如果哈姆的母亲——他母亲(作为孩子替身)搬来会怎样,将她送到老人院又会如何。直到一天上午出现了一次震动,这样的寻常交谈才戛然而止。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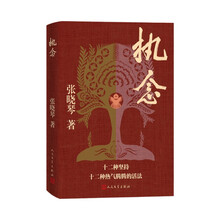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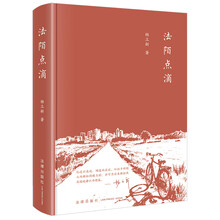
——当代美国作家(约翰·艾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