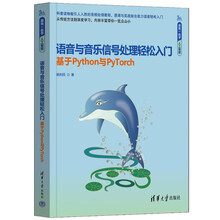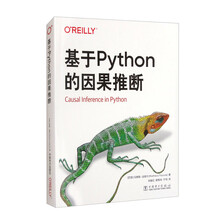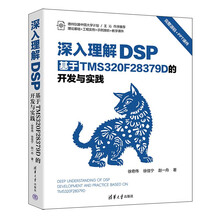第一章 科学家(1946)【部分】
首先我得承认,让我作为“思维的作用”这个系列讲座的一个撰讲人,我感到担忧。因为讨论科学家的创造力这样的问题,必然涉及广阔而又全面的知识,而我深深感到我在这方面不是行家,可能讲不好。尽管我对把我作为这个系列讲座中科学家的代表是否合适感到疑虑,但对选择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作为精密科学的代表,我却没有丝毫疑虑。因为在所有精密科学的学科中,天文学最具综合性。它需要综合各个不同时期的学术成就,以便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另一方面,在所有科学中天文学占有独特地位,诺伊格鲍尔(O.Neugebauer)曾经说过:
自从罗马帝国衰亡以来,天文学是所有古代科学学科中唯一完整流传下来的分支。当然,在罗马帝国残存的地域内天文学研究的水平下降了,但天文学理论与实践的传统却从来没有丢失。相反,印度和阿拉伯的天文学者改进了希腊三角学的笨拙方法,新的观察结果不断地与托勒密的观察结果加以比较,等等。人们只有将这种情形与希腊数学的较高分支的完全失落这一情形加以对比,才能认识到天文学是联系现代学科与古代学科的最直接环节。的确,只有不断地参考古代的方法和概念后,人们才能理解哥白尼、第谷·布拉赫和开普勒的著作,但是,我们要想理解希腊人有关无理数的理论和阿基米德的集合方法,那只有现代科学家在新发现它们后才可能。
这个系列讲座的发起人要求每个演讲者通过阐述其特性、总结其目的以及解释其技巧,来说明他所从事的艺术或职业的价值。在我开始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想提请大家注意并牢牢记住自然科学的总体分类,即自然科学分为基础科学和导出科学(derived science)两类。请大家注意,我没有在“理论科学”和“应用科学”之间做出什么区分。对于后者我不打算讨论,因为我不相信在刻意追求科学的应用中,会发现科学的真正价值。因此我将只讨论通常所说的“理论科学”,我想要大家注意的是,我的分类正是将理论科学分为基础科学和导出科学两部分。尽管无法对基础科学和导出科学给出准确或鲜明的定义,但这种分类确实存在着,并且通过我要枚举的例证,它将表现得越来越清楚。广义地说,我们可以认为基础科学试图分析物质的终极构成和基本的时空观;而导出科学所关心的是,利用这些基本概念将自然现象的各个侧面条理化。
通过这样的叙述,有两点是很清楚的:第一,这种分类依赖于在某一特定时间内科学所处的状态;第二,在分析自然现象时,可能确实存在着不同的层次。例如,大量的现象能够从牛顿定律有效的领域中找到直接和自然的解释。然而,其他类型的一些问题就只能从量子理论中获得答案。既然存在如此不同的分析层次,那么肯定存在一些判据,利用这些判据,我们就能确定,在什么情况下哪些定律是适用的,哪些是不适用的。
至于讲到分类本身,我认为最好的例子莫过于卢瑟福(E.Rutherford)发现α粒子的大角散射。他做的这个实验非常简单。用某种放射性物质发射出来的高能a粒子轰击一层薄箔时,卢瑟福发现α粒子有时被完全弹了回来——这种完全弹回的粒子很少,但确确实实存在。在他晚年(1936年)回想这种现象时。他说:“这是我一生中所遇到的最难以令人置信的事。”他还这样描述过他当时的反应:“其难以置信的程度就像用一发15英寸的炮弹射击一张卫生纸,炮弹反弹回来并击中炮手。”他还写道:
经过仔细思考,我马上意识到这种反方向的散射肯定是出自某种单一的碰撞。经过计算我发现,除非重建一个原子模型。在新模型中原子的绝大部分质量都集中在某个很小的核上,否则是不可能得到这种数量级的散射结果。正是从那时起,我认为原子有个很小但很重的带电质心。我发现,某一给定角度的散射粒子数与箔厚成正比,与核电量的平方成正比,与粒子速度的四次方成反比。这些推论后来被盖革(Geiger)和马斯顿(Marsden)用一系列漂亮的实验证实。
作为所有学科基础的原子核模型就这样产生了。一个唯一的观测和对此所做的正确解释,竟导致了科学思想的革命,这在科学史上也是无与伦比的。
我认为,查德威克(J.Chadwick)发现中子一事也属同一种情形。人们现在相信,中子和质子是所有原子核的基本组成成分。
但是我们不能只根据这两个例子就认为,所有有关基础科学的事例只能在原子物理学的领域中才能找到。事实上,能被称为“基础”定律的首例起源于天文学,我指的是开普勒(J.Kepler)的发现。开普勒对第谷·布拉赫(Tycho Brahe)的大量观察结果做了长时间和耐心的分析后,终于发现了行星运动的定律。后来,开普勒定律又导致了牛顿(1.Newton)著名的万有引力定律,而牛顿万有引力定律两百多年来一直在科学舞台上起主导作用。过一会我还会回过头从不同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但这个例子足以说明,只有在万有引力的领域里天文学才能直接引出具有基础性的结论。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这件事实,水星的实际运动轨道与根据牛顿定律预测的轨道之间存在着细微的偏差,该偏差指出了且随后证实了由广义相对论蕴含的对时空观的根本变革。这一事实进一步说明了上述“天文起源”(即“基础定律首例起源于天文学”)问题。哈勃(E.P.Hubble)发现银河系外星云正在远离我们而去,其远离的速度与它们跟银河系的距离成正比,同样,这一发现颇有可能导致我们基础概念的进一步修改。
我上面所举的几个例子,或许表明了科学的真正价值存在于能直接导致我称之为“基础”进展的追求之中。事实上,有许多物理学家真的接受了这种看法。例如,一位很杰出的物理学家曾经对我说,我早就应该是一个真正的物理学家了。显然,他对于我特别偏爱天文学的事情感到担忧,同时也想鼓励我。我认为,这种态度代表着一种对于科学的真正价值的误解,并且,科学史也会对这种态度提出异议。从牛顿时代至本世纪初,整个动力学和由它演绎出的天体力学都完全是在对牛顿定律的结论做扩充、完善和计算。哈雷、拉普拉斯、拉格朗日、哈密顿、雅可比、庞加莱——他们都乐于将他们科学生涯的大部分精力用在这件工作上,也就是说,用于推广一门导出科学上。对于导出科学的嘲笑,意味着否定了这些人如此严肃认真追求的价值观。这在我看来,简直是荒谬透顶得不值一提。
公正地说,基础科学和导出科学之间很明确地存在一种互补关系。基本概念的有效程度,与它们能分析的自然现象的范围大小成正比。如果限制这些概念的有效范围,我们就会发现其他定律的应用将比我们用过的定律更加普遍。从这种观点来看,科学永远是一个形成过程,正是在这种共同努力去分享科学进展的过程中,科学的价值才能得到实现。我想有了以上一些看法,我就能以一种更正式的方式,叙述我所认为的科学的真正价值,这种价值也正是一个科学家在他的实际工作中所追寻的。
科学的价值在于对自然的一致性的不断完善的认识之中。事实上,这仅仅只是意味着这些价值的获得,或大或小地扩大或者等量地限制了人们关于物质及时空概念的适用范围。换言之,科学家期望在他们的追求中,能不断地扩大某个基本概念的适用范围。在这样做时,科学家试图发现这些同一概念是否存在着某些限制,并试图形成范围更宽和适用性更大的概念。科学家所追求的这些价值,包含在我将讨论的三种不同形式之中,这三种不同形式的标题是:“基本定律的普适性”、“根据基本定律所做的预测”和“由基本定律做出的证明。”
我将通过实例分别阐述它们。
基本定律的普适性通过讲述万有引力定律的普适性,在某种程度上能很好地描绘出引力定律是如何获得普适性的。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