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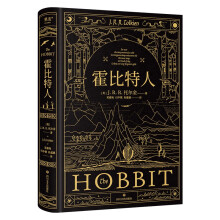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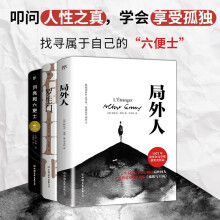





列夫·托尔斯泰是世界*文豪,俄罗斯文学宝库中最明亮的宝石,其作品是深厚的人文主义精神著称。《列夫·托尔斯泰中短篇小说选》精选了这位大作家在不同时期的中短篇小说精品——《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一八五五年八月的塞瓦斯托波尔》《一个地主的早晨》《卢塞恩(聂赫留要夫公爵日记摘录)》《哥萨克(一八五二年高加索的一个故事)》《霍斯托密尔(一匹马的身世)》《伊凡·伊里奇的死》《克鲁采奏鸣曲》《舞会之后》《哈吉穆拉特》。这11篇中短篇小说展现了列夫·托尔斯泰作为一个文学家、思想家的成就。
晚上,等到大门关上,万籁俱寂,花斑骟马又继续讲它的身世:“在我从这个人手里转到那个人手里的过程中,我对人和马做了许多观察。我在两个主人那里待得最久:一个是当上骠骑兵军官的公爵,另一个是住在圣尼古拉教堂旁边的老太婆。
“我在骠骑兵军官那里度过了我一生中最好的时光。
“虽然他是我遭到毁灭的原因,虽然他从来不爱任何人,不爱任何东西,我当时却因此喜欢他,现在也还是喜欢他。他漂亮,幸福,有钱,因此不爱任何人,可我就因为这个缘故喜欢他。你们了解我们做马的这种高尚的感情。他的冷酷,他的残忍,我对他的从属地位,使我特别爱他。在我们美好的日子里,我有时想,‘打死我吧,赶死我吧,我会因此觉得幸福的。’
“领班马夫以八百卢布的代价把我卖给马贩子,骠骑兵军官又从马贩子那儿把我买下来。他所以把我买下,因为谁也没有一匹花斑马。这是我最美好的时光。他有一个情妇。我知道这件事,因为我天天把他送到这女人那儿,或者把这女人送到他那儿,或者把他们俩一起送到某个地方。他的情妇是个美人,他是个美男子,他的车夫也是个美男子。因此我全爱他们。我的日子过得不错。我的生活是这样的:一早马夫就来给我洗刷,不是车夫,是马夫。马夫是个从农夫中挑选出来的小伙子。他打开房门,放出马的气味,铲掉马粪,解下马衣,用刷子刷我们的身体,又拿马篦篦下一条条白色的污垢,敲落在被马蹄铁踩坏的地板上。我开玩笑地咬咬他的袖子,顿顿脚。然后他把我们一匹匹带到一大桶冷水旁边。那小伙子就欣赏着被他洗刷得光滑发亮的花斑,欣赏着那蹄子很宽的像箭一般直的腿,欣赏着光滑的臀部和背——简直可以在那上面睡觉呢。他们把干草堆在高高的栅栏后面,又把燕麦倒在栎木食槽里。车夫头费奥芳也常常到这里来。
“主人和车夫很相像。两个人都是天不怕地不怕,都是除了自己谁也不爱,因此大家都很喜欢他们。费奥芳穿着红衬衫、黑绒布灯笼裤和腰部打褶的外衣。我喜欢他开玩笑。有时过节,他穿着这种腰部打褶的外衣,身上涂了香油,走到马房里来,大声叫道:‘喂,畜生,你忘啦!’说着又用草叉柄戳戳我的大腿,但总是一点也不痛,他这只是闹着玩的。我立刻明白他是在开玩笑,我就贴起一只耳朵,龇龇牙。
“我们那里有一匹拉双套车的黑驹子。他们常常在夜里把我同他套在一起。这怪物不懂得开玩笑,却凶得像恶鬼。我同他并排站着,中间隔开一道矮栅栏,有时我们就认真地相互咬着,闹了起来。费奥芳可不怕他。有时候,他一直走过来,大喝一声,仿佛要揍他,其实并不,费奥芳只是给他戴上笼头。有一次我同他一起拉车奔下库兹涅茨桥。主人也好,车夫也好,他们都一点也不怕,两人都笑着,吆喝着桥上的人群,驾驭着,转来转去,因此没有轧着一个人。
“我为他们效劳,牺牲了我最出色的长处和半条性命。当时他们给我饮水饮得过了头,赶路赶断了腿。尽管这样,这还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他们总是在十二点钟来套车,给我的蹄子抹上油,前额和鬃毛洒上水,把我拉到车辕里。
“雪橇是柳条编的,上面铺着丝绒,挽具上有小巧的银扣子,缰绳是丝织的,一度还是抽花的。套具是那么合身,等所有的缰绳和皮带系住扣好,简直分辨不出哪里是套具,哪里是马的身体。他们总是毫不费劲地在棚舍里把车套好。费奥芳走出来,他的屁股比肩膀还宽,肋下束了一根红腰带,察看了一下套具,就坐下来,掖起长袍,一只脚伸进踏镫,总是说句把笑话,挂上那条从来不打我、只是做做样子的鞭子,说声‘走’!我慢吞吞地走出大门,每走一步都耍些花样。厨娘走出来倒泔水,总要站在门口瞧一瞧。农夫扛柴火到院子里,总是把眼睛睁得老大。我出了大门,跑了一程,又停下来。仆人们走出来,车夫们把车赶在一起,攀谈起来。大家一直等着,有时我们在大门口差不多站上三个钟头,偶尔也有跑上一阵,转个弯,又停下来的。
“最后门口传出响声,头发花白的吉洪穿着燕尾服,挺着大肚子跑出来,叫道:‘过来吧!’当时还没有那种愚蠢的说法:‘前进’,仿佛我不知道拉车不能‘后退’,只能‘前进’似的。费奥芳咂了一下嘴,车子驶了过去,公爵神气活现地匆匆走出来,仿佛无论是雪橇、马儿,还是那个弓着背、吃力地伸着双臂的费奥芳,都平淡无奇,不屑一顾。公爵头戴高筒军帽,身穿皮大衣,灰色的海龙皮领子遮住他那眉毛乌黑的红润的漂亮脸儿——这么漂亮的脸儿是永远不该遮住的。他走出来,军刀、马刺和铜鞋跟碰得铿锵作响。他匆匆从地毯上走过去,根本不理我,不理费奥芳,不理大家所感兴趣的东西。费奥芳咂了一下嘴,我拉紧缰绳,恭恭敬敬地把车拉到门口停下来。我瞟了一眼公爵,扬了扬头和细长的额鬃。公爵情绪很好,偶尔同费奥芳开个玩笑,费奥芳稍稍转过他那漂亮的头,回答着。他没有放下手,用缰绳做着只有我能勉强察觉和懂得的动作。于是一、二、三,我抖动身上的每块肌肉,把雪和泥浆往雪橇的前部踢去,步子越来越大地向前奔驰。那时也没有现在那种愚蠢的叫法:‘驾!’——仿佛车夫身上什么地方作痛,那时都含混地叫:‘喂,小心啦!’费奥芳就叫起来:‘喂,小心啦!’于是行人闪到一边,站住。他们都歪着脖子瞧着漂亮的骟马、漂亮的车夫和漂亮的老爷。
“当年我最爱超过别的快马。有时候,我同费奥芳老远看见一辆值得追赶的雪橇,我们就像一阵风似的追上去,渐渐地越来越接近它,我把泥浆溅到那辆雪橇的后背,同那雪橇上的乘客并驾齐驱,我朝他头上打了个响鼻,接着又同辕鞍、同车轭并齐,后来就看不见那雪橇,只听见它落在后面越来越远的声音。而公爵、费奥芳和我都不作声,装成我们只是在赶路,根本没注意那些在路上遇见的驾着劣马的人的样子。我喜欢超过人家,但我也喜欢遇见好的快马;只一刹那工夫,一个声音,一个目光,我们就分道扬镳,又单独地各奔前程了。”
译本序
十二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五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一八五五年八月的塞瓦斯托波尔
一个地主的早晨
卢塞恩(聂赫留朵夫公爵日记摘录)
哥萨克(一八五二年高加索的一个故事)
霍斯托密尔(一匹马的身世)
伊凡·伊里奇的死
克鲁采奏鸣曲
舞会之后
哈吉穆拉特
不认识托尔斯泰者,不可能认识俄罗斯。
——(苏)高尔基
我认同托尔斯泰的精神世界。他主张要爱一切人。世界上每个人活得都不容易,哪怕是坏人,观察他的全部人生,也有怜悯的必要。怜悯也是一种爱。爱和被爱才是我们人活着应该争取的。
——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家:周大新
我始终相信,他是赢得最多作家的尊敬的一个作家。没有一个人敢于用轻薄的口吻谈论他,没有一个当代艺术家不去仰视他。他的天才、难以企及的技巧,比起他的伟大人格,似乎都是可以略而不谈的因素了。没有人敢于断言自己比他更爱人、爱劳动者,比他更仇恨贫困和苦痛、蒙昧。
——中国作协副主席:张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