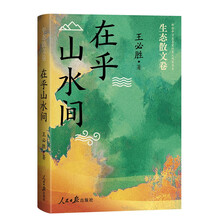《浅水不养山》:
在生命的旅程中,我深深地铭记着"2008”这个异乎寻常的年份。的确,2008无论于我个人还是于国于民,似乎都堪称祸福相依,悲喜参半。不约的是汶川大地震的突如其来,约定的是北京奥运会的成功举办乃至完美收场,这既是国家的大事记,也是本民族一悲一喜都打破了纪录的经历。而具体到我个人,2008于我也同样是吉凶交替、荣衰互访。好比人在旅途遭遇两盏灯,一盏绿色通畅,另一盏却又刺刀见红。是的,那一年“羊”来了,“狼”也来了,只是“羊”来得十分华丽,而“狼”来得却多了几分惨烈。
无论从东方文化说,还是从西方文化说,“羊”都意味着一种善。对于国人而言,与生俱来的天性似乎就是羊性十足,所以每每看到天上的白云,往往就会不由得想到羊群。小说家潘军的小说《小姨在天上放羊》就有指云为羊的意味。古代的罗马人也有见羊为福的习俗,在宗教文化里就更不用说了,羊就是耶稣基督的代称,不仅是吉祥的象征,而且也是抑恶崇善、穷尽仁爱于天下的集中体现。而“狼”无论于谁,无疑都意味着一种不祥乃至凶相毕露。2008,“羊”与“狼”的“轮回”于我,似乎都在意外,并不在意中,也就是说都不在生命的预约之中。
2008,似乎注定就不是一个寻常的年份。作为一介苦坐书斋、动辄突发奇想于笔端的书痴,我进入2008伊始,除了深深坠入了奥运氛围之中,别的私下生活似乎也无异于常形常态,可以说没有任何约定的人和事,尽管有某些挥之不去的心理期待悄然渗透心底,不过人之常情,却也不是能够约定的事。
然而,生活中“羊”的光临有时候并不打招呼,是那样悄然无声。大约是那一年冬去春来的一天,我意外地接到了来自加拿大温哥华的一份邀请函,有一个关于平民教育问题的学术研讨会邀请我前往出席。
除了往返机票费用自理,其他入境费用均由邀请方承担。当然,天上掉馅饼也并非无缘无故。邀请方是加拿大文化更新研究中心,该中心系爱国华侨、海外著名文化学者梁燕城博士创办并被加拿大政府认可且享有广泛声誉的文化基金会所属,其会刊《文化中国》(学术季刊)已在加拿大华人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或许是因为我在这本刊物上连续发表了几篇论文而引起了该中心的关注,所以才收到了被该中心热忱邀会的橄榄枝。
前往加拿大温哥华的前前后后,一路都是绿灯,在各方面的呵护成全之下,温哥华之行顺风顺水,可谓遍地都是“羊”群。尤其到了温哥华之后,乐善好施者随处可遇。比如在温哥华机场出站时手机不支持,与接站人员联系不上,正在这时一个陌生的华侨主动走过来帮我投了一枚加币开通了公用电话,于是燃眉之急就被转换成了绿色通道。这一小小的善举于我实在不啻一片沙漠之中突现一片绿洲,对于生命无疑是一个透心透肺的滋润。前来接站的子夜先生系《文化中国》的主编。这位来自华夏的加拿大华侨在接待安置与会人员的过程中,简直就是一个善的天使,总是穷尽其善去满足每一个需要帮助的远方来客。子夜先生为人笃实、诚信、大度而且谦卑,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他的身上得到了无价的保险抑或保留。他特别善解人意,在温哥华小住的几天里,我所亲临其境的几个著名景点,都是在子夜先生的撮合与成全之下实现的。而在市内,其人其车几乎就成了吾的专用,每日里什么时候需要他就在什么时候出现,总是神灵一般与吾心心相通。每次服务上门都不见丝毫倦意及其拒扰之态。那几天耗掉他的人力物力(包括车油费)差不多相当吾国内一个月的工薪收入了。这事至今回想起来仍不免有一些歉意滞留心中。
在温哥华感受仁爱友善的经历不胜枚举,但让我的生命为之震撼的是那一天由子夜先生驾车带我去拜访在温哥华定居的台湾著名诗人痖弦先生。这一见具有活生生的戏剧性。我与痖弦先生神交多年,却一直未曾谋面。直到2008那一年有幸实现温哥华之旅,才从子夜先生那里得知痖弦先生退休之后就定居在温哥华,而且就住在温哥华三角洲一处。他们还见过几次面。这消息于我无疑是一大惊外之惊、喜外之喜。自然,到温哥华拜访诗人一事,就成了心中的一大“块垒”。在子夜先生的成全之下,我如意地在大洋彼岸见到了仰慕已久的大师尊容。只是那一天我所见到的痖弦先生,已不见激情满怀、诗意盎然的诗人风采了,已年过七旬的老人在那一天流露出来的情感意绪,除了接人待物的几分热诚与礼仪,另外幽幽沉淀在眼底的就是一种难以掩饰也难以言尽的忧伤。坐下来长聊时方知,诗人深爱的妻子张桥桥两年前因病不治而撒手西去,老人至今仍然深深地滞留在无尽的思念与哀痛之中。说起张桥桥,诗人满怀深情地告诉我们:桥桥本来是个才女,写得一手好文章,在台湾文坛也小有名气。可不幸的是,还正是豆蔻年华,十九岁的她就得上了肺病。此病纠缠如毒蛇,一旦缠上身,就执着如冤鬼。在他们的相识相爱的漫漫岁月里,桥桥一直都是个病号。最后十年都是靠吸氧维持生命,直到六十四岁那一年去世。诗人之所以多年前就顶着经济压力在温哥华买房定居,也正因为张桥桥身患此种顽疾,而温哥华的空气干净,其清洁程度在世界上数一数二。选择定居温哥华,对于患有肺病的张桥桥来说,是这个世界任何瑰宝都不可替代的馈赠了。说到张桥桥的死,老人显得十分凄然,以致坦言张桥桥的死对他的打击太大,一种莫名的孤独感时常悄然袭来,俨然这个偌大的世界转眼之间就剩下了他一个人,一切都变得那么空空荡荡了。张桥桥虽然已去世两年多,但张桥桥生前使用的钢琴、喜欢的一幅书法作品(为张桥桥生前好友董阳孜女士所书的“桥园”二字)以及张桥桥生前孜孜信奉的耶稣受难图,都还原封不动地定格在那里。从老人的眼神里,我们完全可以读出其不言的心曲:每每看到这些张桥桥生前的爱物,对于老人来说,就如同生活中还有知心知肺的张桥桥的相依相随,这份守望似乎永远也难以割舍。
那天与诗人告别之后,我和子夜诸君在打道回府的路上,心里也不免多了一份念叨,人生苦短,晚来凄凉,生离死别之悲情,普天之下,谁也无可抗拒,这就是所有人的宿命!善固然是美的,可有时又多了些酸楚。如果说,在痖弦先生那里善多了些酸楚,那么当我们见到梁燕城博士时所领略到的种种善行义举,善就多了些刚性的质地乃至壮丽的风姿。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