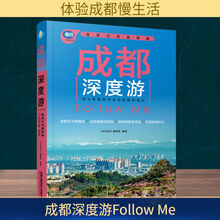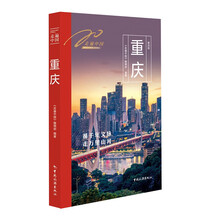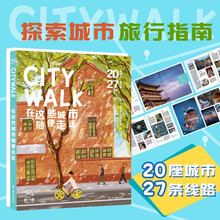当时我有瞬间的惊异:这首诗,太杭州!
接下来就断续地关注和阅读张岱。感觉这个人似明末的幽灵,终日飘荡在这片湖山,每一寸土地,每座山,每棵树,每个寺,每条路,每架桥,甚至,西湖水面的一纹一波,就像他手心的纹路,信手拈来,脱口而出,不似我等动辄查阅资料,这样的一个湖痴就疯疯癫癫地立在眼前。
走在西湖,张岱的影子就是太阳的影子,走到哪里别想摆脱。手中有一本薄薄的《西湖梦寻》,把西湖里里外外上上下下说个通透,许多地名我都是首次听说,有时就想按文索骥去遍访,可是一是时间有限,纵使有时间,简直迷了路花了眼。像这些大众性的如玉泉寺、孤山、苏小小墓、葛岭、苏堤,自然不用引路,可是太多的生避地名,如哇哇宕、韬光庵、岣嵝山房、紫云洞,倒不是不能找到,肯定要颇费工夫,像我这般浮躁心境已经失去了耐心,除非退休后,万事皆休,方可迈动不太灵便的双腿去寻吧。
即便这样,我还是像仰视苏东坡白居易一样地仰视张岱。这也是一种精神,何况,西湖天下景,张岱眼中的“景”就是能够出奇出新,比如《湖心亭看雪》,“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
读到此每每称奇,人以“粒”为量词,那种湖天一色、万迹皆绝的空旷静寂,谁人能如此描摹?这等奇思妙想空灵诡异,非张岱,无人能出其右。
当先人们将这个世界的芸芸众生参得只剩“一粒”,我很想知道,他们眼中,这个世界的样子。
再看《玉莲亭》,同样的白居易守杭州,人们大多记得他未能抛得杭州去、孤山寺北贾亭西、万株松树青山上,可在张岱眼里,白居易是这样“施政”的,“白乐天守杭州,政平讼简,贫民有犯法者,于西湖种树几株;富民有赎罪者,令于西湖开葑田数亩……”我看到这里心中一乐,世间还有这样的刑罚!种树、开田也算服刑,亏白居易想得出,文人当政自有其独树一帜的奇绝,难怪数年后,“湖葑尽拓,树木成荫,乐天每于此地载妓看山,寻花问柳……”读到这里,我更是乐不可支,原来,这白乐天真真乐天!谁说今人懂得享受生活,你看一千多年前的白乐天比今天的官员毫不逊色。幸亏张岱的“挖掘”,我们才得知,也许你漫步湖边的时候,某棵弯腰吻水的老树就是一千多年前的某犯人所栽,待到几百年后北宋的苏轼疏浚西湖时,原有前朝的罪民已经为西湖打下基础,故而苏轼之于西湖才有特别的意义,而相对于白市长的“绝活”,真是小巫大巫了。
像张岱这般空灵妖异,我身边还真有这么不羁的一“粒”。
我的这“粒”朋友属于处处从心出发的人。此刻她隔了千山万水打来电话,急火火地说,赶紧上网,看一个节目,《台北故宫》。
这一“粒”,我不敢说懂她百分之百,90%以上还是把握的。由于她一直以来对书画、考古的迷恋而储存了满腔的爱意。别误会,这是一种泛爱,对艺术的痴迷使她超越了男女两性,由考古而音乐,龙山文化、良渚文化、红山文化,玉璧、玉琮、玉钺,还有一堆我叫不上名字的古文化术语,每天早晨5点起床,非常固定地坚持练习6个小时书法,读规划中的艺术理论书籍。忽地一转身,又抱起古筝疯了一般练起来。
在我面前,她就像一条鱼,倏地一跃而起投入到艺术的汪洋大海。
和她相比,我简直俗得掉渣。关于“台北”的信息也许只关注了一下沸沸扬扬的“售武”事件,如果再有就算得那边的旅游信息了。至于台北的“故宫”,压根就没进入过我的视线。
我接她电话的刹那,正在兴致勃勃地带女儿站在城隍阁最高处面向西湖观察那里到底几粒人,雨线如织不说,城檐下的风呼呼作响,她的电话时断时续,但我还是感到了她的哭韵——那可不是悲痛与哀伤,而是激动幸福——喜极而泣。
她说,她只看了一个片头,就哭得一塌糊涂。她还在电话里梦呓一般:溪的美,鱼知道……风的美,山知道……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