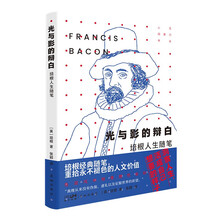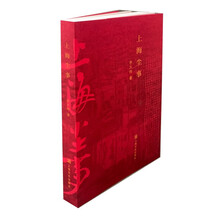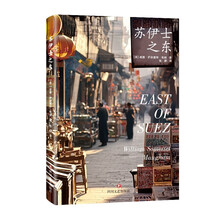年好过,春难熬。青黄不接的春天煎熬着人们的肚皮和意志。吃饭问题,成了家家的心结。大爷爷忍受不住饥饿的煎熬,拖家带口闯东北时,撂给我爷爷和胡同里的三爷爷一句:“养好老娘。”之后,一去多年杳如黄鹤。八十多岁的老奶奶老眼昏花,摸索着来到三奶奶家要一筐煤做饭,三奶奶翻着白眼珠一句话呛死人,她说:“我一个荒草叶子盖不过腚来,哪有炭给你?”老奶奶踉踉跄跄回了屋,老泪横流。
“连娘都不管,还有人味儿吗?”爷爷气得跳脚骂。此后,老奶奶的衣食用度落到了母亲头上。每天母亲做好了饭总是先给老奶奶端过去一碗。那时,爷爷没白没黑地干满一天,只挣8分钱,幸亏我们姐弟年纪小、饭量小,才不至于吃了上顿没下顿。
爷爷争强好胜,农活儿样样精通,那铁打的身板无论干什么活儿都是手脚麻利,风卷残云,他一个人顶三个壮劳力挣工分:一早一晚在牛栏院挑水、铡草、喂牛;牲口出了工,他就跟到地里干活儿:农忙时他又担任场长,督促社员打场、晒粮。
仓促的麦收时节,家家户户像上紧了发条的闹钟,一步不落地追着天气赶。洗洗涮涮,缝缝补补,忙忙碌碌,母亲像追着碌碡跑的人,从家里转到地里,从堂屋转到灶房,一天到晚总有干不完的活儿。那天早饭后,母亲急急火火赶到场院时晚了几步,爷爷迎头一声呵斥:“都什么时候了?才来干活?”尴尬的母亲扛着木锨转身回了家,紧跟在后的大婶儿牢骚满腹,也嘟嘟嚷嚷回了家。母亲和大婶儿的半天工分泡了汤。
晚上,爷爷满身疲惫回到家。一口热茶还没进肚,爷爷点着旱烟袋就数落上了母亲:“以后甭干这站不住理的事儿。你晚了,这工分怎么算?”“四婶子那天不是也晚了吗?”母亲的话音未落地,爷爷“哐”的一声,铜嘴旱烟袋磕在八仙桌上,他说:“兴别人这样干,不兴咱!”母亲不再吱声,慌忙收拾饭桌。
白天,爷爷在场院里于疯了,一个人站在高高的脱粒机旁扬场,扬出了六千斤麦子。机器轰鸣怒吼,飞速旋转吞咽着麦捆。爷爷扒光了脊背,甩开膀子大干了一天。汗水混合着泥土,从爷爷黑红铁打的脊背上向下流,头发、眉毛、络腮胡子上落满了长长短短的麦秸。一锨麦子还没在簸箕里落稳,爷爷轮开双臂一扬抛到半空,麦糠顺风飘出去,麦粒雨“唰啦啦”落在地上。两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轮流上麦子,也没赶上爷爷的速度。阴历六月天,毒辣的太阳炙烤着大地,最调皮的孩子也不敢赤脚在滚烫的地面上乱跑。树叶蔫了脸,蒙着一层灰尘。场院里,忙碌火辣的气氛让人恐慌。六月天,娃娃脸,说变就变。说不准什么时候一阵狂风暴雨,忙活半年,盼望半年的麦收就会泡汤。这救命的粮食没进仓,爷爷心里不踏实。爷爷心疼粮食,更敬畏粮食。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