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完父亲的电话,我只能苦笑:我害怕父亲的电话。每次接到父亲的电话,我都心情变得极度颓败,如果儿子可以告父亲电话骚扰的话,我将去申告。可是我怎可以置父亲的感情于不顾呢?况且我又如何不理解父亲此番寄情于我之切切的心理呢!一个经历着悲欢离合的家庭对于希望之渴求又是何等之强烈啊!
父亲差不多每周给我两个电话。询问的内容无非是我的工作如何、是否有女朋友、现在在千什么以及有没有什么好消息等。这些问题,程式固定,久而久之,如同一则没有艺术感的广告一样叫人抓狂。我只能支支吾吾地回答父亲,简直不能让他高兴。他希望我能挣更多的钱,尽快改善生活条件,将破败的家庭改头换面,彻底洗刷掉家庭在乡里的耻辱。在外流浪、寄居的生活让他内心悲凉,他将希望寄托于我,至少我是他的希望之最大的载体。他至今仍辛劳地工作着。当然,他也知道怎样保存自己,怎样快乐一点。他比我母亲聪明多了。
我时常想,如果没有发明电话就好了,或者电话的资费再高一些就好了。那样或许可以更自由一点。但父亲的电话是一个严肃的伦理问题。一个选择远离父母的年轻人,父母只能通过电话来沟通到他。所以电话沟通成了必然要发生在父子之间的事情。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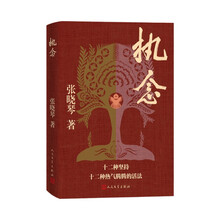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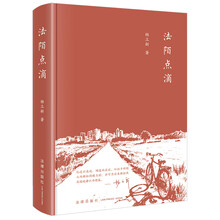
——朱正琳(著名学者、书评人)
经年不联系的小友发雷,忽而发给我这么一大部书稿,我才知道这后生端的在火热地生活着,而且活得比绝大多数人都本色,都精彩,超出了我的期望:他有点像俄国作家,与这致命的土地和生活拥抱、撕咬、扭打,在这斗争中,他很像“人”了。荷尔德林说:“成为了人,就成为了神,只有神才是美的。”
——何三坡(著名诗人、批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