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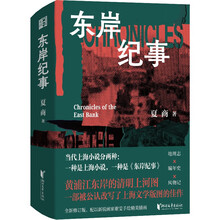




《鱼王》包括三个中篇小说,《鱼王》、《鹰王》、《豺》,都以云南山区为背景,写传奇人物与传奇动物之间的故事,情节因此也具有传奇性。如《鱼王》中白水湖里无比巨大的鱼,《鹰王》中象征神秘、高贵和自由的鹰,《豺》中始终潜伏的凶险的豺狗。与传奇人物和传奇动物相对的,是短视好利的庸常民众,作者以入世未深、淳朴尚存的小孩子的眼,写出双方的矛盾和故事的发展。
小说的主旨在于,在物欲、贪婪填塞心灵的世界,神话和传说的死去。但那些传说,或者那种神秘的(拥有神性的)、使人敬畏的东西,终究还不是完全死亡、散落,还留下了一些微薄的希望和安慰。
最初的黄昏是一条很淡的线,从西山头无声无息地滑下,渐渐地,汹涌起来,很快淹没了整个坝子,黑压压一大片,漫到东山脚,我们知道该回家了。我们牵着牛,挽着马,撵着猪,浩浩荡荡回山下的家,不断招呼还不打算回家的伙伴。回去咯,回去咯,呼喊声四处传出,口哨声此起彼伏,夹杂着满山满林脆亮的鸟啼。鸟啼一声高过一声,口哨也一声高过一声。傍晚灰蒙蒙的阳光下,寂寂的山林一下子喧腾了。我们下了小山坡,一眼就望见那片白亮的湖水。湖面夕光粼粼,好似一尾尾红鲤鱼跃出水面又钻入水底。我们立住脚,望一会儿湖水,湖水把眼睛浸得湿漉漉的。不少人想起两年前的白水湖,那时候的白水湖清亮、热闹,鱼王的传说让人满怀想象。现在,传说消逝在涟漪之中,记忆消逝在时间里,白水湖仿佛抽掉筋骨的人,显出倦怠的面容。那时我们也不用到远处的山坡,只消将牛马猪羊撵到湖边,就可以撒手不管了,牲畜们才舍不得离开湖边水嫩的青草呢。我们打牌,钓鱼,脱得赤条条地游泳,游完了又站上岸边的大石头,八叉着腰,腆着肚子,朝水里撒尿,叮叮咚咚,撒完了又扑通一声跳进水里,肥大的水花白生生地簇拥着我们古铜色的小身子。
从我们记事那天起,山半腰的白水湖就是我们这一村的。父辈们、祖辈们也说,打他们记事起,白水湖就是我们这一村的。这么说来,尽管时间已经面目全非,许多事是不会改变的。那时候我们相信这种状态会持续下去,直到两年前那个早上。
一大清早,我们醒来后,看见村长出现在院子里。村长对父亲母亲说:“从今天起,你们和自家小娃说说,不要到白水湖游泳了。”我们的父亲母亲眼角糊着黄眵,眼神像蒙着一层纱布,呆得像两段木头。村长补充说:“村里把白水湖卖了,卖了十年,人家在湖里养鱼,小娃再到湖里游泳就不好了。”
这时候,我们的父亲母亲才擦干净眼睛,看到村长身后闪出一个男人。男人比村长矮半个脑袋,却差不多有两个村长那么粗,宽手大脚,脖子短粗,脑袋浑圆憨实,好比一大颗熟透的南瓜搁在木墩子上。他望着我们的父亲母亲,肥厚的嘴唇朝两边拉了拉,做出一个笑的动作,突然,两手歘地叠在一起,朝父亲母亲铿锵地举了举,用一种陌生的方言洪亮地说:“我姓刁,叫我老刁就成,往后全靠你们了!”老刁的动作和声音来得太突然,太像电视里的场景了。我们看见父亲母亲轻微地抖了一下,惶遽地向两边躲闪着,嘴巴张开,嗯嗯啊啊不知说什么好。
我们对老刁的第一印象走了两个极端。有人对他崇拜得五体投地,把他和心目中的英雄人物归到一块儿,人前人后学他:两手歘地叠在一起,举一举,大声说,往后全靠你们了!学完再也憋不住笑。也有人听了父母的分析,对老刁怀有相当大的戒心。他们的理由很多:首先,老刁的姓就有问题,只听说过姓张姓李的,他姓什么刁?大家又都知道很著名的刁德一,不能不让人生疑;其次,他们认为老刁到每家每户来那么一套,明面上是向各家各户打招呼,实际上是警告各家各户;最重要的一点,原本是全村人的白水湖,一夜之间,什么风声也没听到,就变成他的了。白水湖不再是我们的了。
起初我们对最后一点没有足够的认识,后来越想越不是滋味,又都不相信。什么都能卖,那么一大片水,怎么卖?又怎么在里面养鱼?当天下午放学后,我们又牵了牛,挽了马,撵了猪,接二连三走出家门。“去哪儿?”我们相互打着招呼,比往日热情、激动。“去白水湖啊!”没人回答别的。
白水湖还是老样子。一大片白水汪在群山间,黑的山影静静倒映在湖心,山风穿过松林,从湖面刮过,掀起一层细细的涟漪,如一群银白背脊的鱼迅速跃过。我们的心安定了。我们把牲畜撵到湖边水草丰盛处,可一时想起早上的事,心里又有些不稳妥。我们沿湖边走,试探着,侦察着。走着走着,一阵风吹来一些声音,是斧头吃进木头里,“笃——笃——”,很有力量,一下是一下。我们以为有人偷松树,走近一个小山坳,才发现声音是从里面传出来的。不到一天的工夫,山坳里平地起了一间空心砖小屋。四面墙打好了,两个人正在摆弄一堆木头,看来是要给小屋做屋顶。我们看清楚了,其中一人正是老刁。老刁身边站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男孩短粗精干,我们一眼就看出来,他是老刁的儿子。
我们站在湖边,一排脑袋仰着,目不转睛地望着他们。男孩先发现了我们。他扭过头,怔怔地望着我们,我们也望着他,他迅速低下头,嘴凑到老刁耳边。老刁扭过身子,斧头横在额头,冲我们大声喊:“上来嘛,上来!”我们保持着原来的姿势,任凭老刁的声音在耳朵里嗡嗡回响。斧头的刃口在阳光里刺啦亮了一下,有人眯缝起眼睛。老刁站起来,斧头划出一道明亮的弧线。老刁又喊:“上来嘛,上来!”我们吸吸鼻子,看看彼此,脸上泛起一丝得意的表情。
老刁是干活的好手。我们围成一圈,眼睛都看直了。老刁松松握住斧头,把疙里疙瘩的原木削得光滑浏亮,又抄过锯子把长长的木棒断开。锯子发出纯净而持久的鼾声,声音高上去,又低下来,老刁龇着牙,上身俯下去,又直起来,我们的视线追随着老刁握锯把的大手,脑袋不自觉地移上移下,如同小鸡啄米。只有老刁的儿子一动不动,两手扶着木头,垂着脑袋盯住裂口落下的木屑。木屑潮湿、金黄,均匀地铺在地面,不多一会儿,铺了鞋底那么厚一层,散发出微带苦涩的清香。老刁锯好椽子,又拿凿子凿了眼,之后就开始往房顶架。我们完全忘了试探,心全然沉浸在对老刁的钦佩里了。我们掩饰不住兴奋,跟前跟后,希望老刁派给我们一项任务。不多久我们就发现了自己的无用。我们总是忙忙叨叨,叽叽喳喳,打翻墨斗,撞倒锯子。而老刁的儿子一句话不说,沉静地跟随老刁,只要老刁一伸手,他立马把东西递到老刁手中,件件是老刁想要的。我们停下来,看着他,想弄清他如何看透老刁的心思,他见我们看他,迅速低下了头,脸从耳朵红了起来。
钉好椽子,得把石棉瓦放上去。老刁站在屋顶,我们往上递。石棉瓦很重,老刁的儿子一个人搬有些吃力,我们不等老刁吩咐,早七手八脚和男孩一齐搬起石棉瓦,做出很吃力的样子,把石棉瓦高高举到老刁眼前。老刁的手一碰到石棉瓦,我们便轻松了。老刁说:“辛苦了!辛苦了!”我们的脸通红通红,小小的心脏激动得一个劲儿乱蹦。
火烧云满天,落日染红湖水的时候,小屋仿佛雨后冒出的第一朵蘑菇,那么小巧、别致。我们走进小屋看看,又走出小屋瞧瞧,一想到小屋的建成有我们的一份功劳,心就满满的。我们磨蹭着,舍不得走。老刁忽然想起了什么,说:“你们先不要走。”转身进了小屋,在一担行李中摸索。我们充满期待地望着他的背影。老刁走出来,一双大手捧着堆尖的花生。老刁把花生推到我们面前,客气地说:“辛苦了,没什么好东西谢你们,随便吃点儿。”我们在裤子上擦着手,久久不肯伸出去。最后,我们每人抓了一大把花生,面朝湖水,坐成一排,嘴里发出一片磕巴磕巴声。我们吃了嫩嫩的花生,奋力将壳朝湖水扔过去。老刁和他儿子则把花生壳堆在脚跟前。我们看到,他们父子俩的脸是如此相似,湖水反射着通红的夕光,夕光照亮他们饱满黝黑的脸庞,一阵山风吹过,夕光晃动着,他们的脸也晃动着。
我们回家时夜色已经浸进湖里了。前脚才进家门,我们便迫不及待地讲白天的事,没想到大人的态度很让人扫兴,他们听完后,要么不发一言,要么阴着脸说:“小娃家晓得什么!”
第二天,我们迫不及待地来到湖边,老刁远远望见我们,很热情地朝我们招手。紧挨昨天盖好的小屋,老刁和儿子又在盖另一间,盖好后,太阳还剩一大截。我们像头天一样,没有立即走,我们的等待有了具体内容。老刁呵呵一笑,很豪迈地挥挥手,说“算了算了”,转身进屋,又捧出堆尖的花生。
就在我们大声“呸呸”着,朝湖里吐出花生壳的时候,一头水牛大摇大摆朝湖里走去,湖水很快淹没了它的整个身子,一层层涟漪的中心是它昂起的大黑脑袋,它一边悠然地往水深处游去,一边很响亮地喷着鼻子,“噗突突——噗突突——”黢黑的脊梁偶尔凸出水面,乍看上去,还以为是传说中巨大无比的鱼王呢。我们对这种场面早习以为常,这时候当着老刁的面,心里却莫名地得意。三皮倏地站起,哈哈笑着,扔掉花生壳,朝水牛奔下去,一路上甩掉了衣服、裤头,我们听见他的光脚板啪啪拍打着草地,嫩草芽儿溅出绿草汁。接着,扑通一声巨响,白亮的水花溅起。三皮细细的胳膊在水花中舞动着,脑袋葫芦似的,浮起来又沉下去。三皮很快抓住一只牛角,牛摇摆脑袋,哞哞叫唤,想要摆脱他。他不慌不忙,随着牛的摆动调整身体,我们知道三皮在炫耀自己的游泳技巧,更得意了。我们偷眼看老刁,不知怎么回事,老刁板着脸,并不看我们。闹腾得四周的水浑浊了,三皮才狗刨着水,身子朝后缩了缩,一只手搂住牛脖子,一只手拽住绳子,翻身骑上牛背,让牛转回头,朝岸边游回来,一只手高举着,向我们大声打招呼。我们也向他举起一只手。落日的阳光铺满湖面,三皮疮疤遍布的小身子熠熠闪亮。
我们又偷偷看老刁,老刁嘴角抽动着,眼神茫然。老刁的儿子焦急地望着湖水,一只手被老刁牢牢拽住了。
三皮牵回自己的水牛,湿淋淋上来后,我们围着他欢呼雀跃,声音在大山之间久久回荡,在湖面激起细小的涟漪。老刁干干地笑了两声,拍拍三皮的肩膀。三皮咧着嘴,一副讨好的样子。
回到家后,我们不像头天那样,对白天的经历充满表达的欲望,心里头闷闷的,对父母的疑问置之不理。
我们再来到湖边,没看见老刁和儿子盖房子,他们似乎不打算再盖第三间房子了。他们在湖边忙碌,一些粗大的钩担竹躺在身边。我们静静看着,老刁和儿子吃力地拉着锯子,竹子不时涩住锯子,锯子发出的鼾声时断时续,锯口断断续续落下一缕缕淡绿色的潮湿粉末。老刁吃力地朝我们笑笑,老刁的儿子绷红了脸。
我们问老刁:“你们做什么?”
老刁不回答,把锯子拉得山响,咔哒断开竹子,喘了一口气,大声说:“筏子!”
我们的兴奋是不消说的。我们只在电视里见过筏子。老刁扎好筏子,我们一致认为,老刁的筏子比电视里的筏子更像筏子。筏子推入水中,我们谁都想挤上去,又都有点儿担心,怀疑湿竹子能不能受得住我们。正当我们推推搡搡时,老刁从屋里拿来一根细竹竿,一点,唰地一跳,身子稳稳当当落在筏子上。筏子荡着,扩开一层层涟漪。
老刁笑眯眯地说:“成了!”
我们欢叫起来。但老刁没让我们上去,他把筏子荡远一些,望着我们。
“你们想坐筏子?”他说。
“那还用说!”我们尖声叫着。
“那你们得答应我,”老刁沉吟着,“今后不要让牲畜下到湖里,你们也不要到湖里游泳。”我们沉默了。
老刁又说:“白水湖还是你们的,不过白水湖下头就是滚石河,你们游泳可以到河里嘛。”——我们还能说什么呢?
我们一一上了筏子,小心稳住身子。最后上的是老刁的儿子。老刁说:“海天,回去拿瓶酒来。”我们这才知道这个沉默寡言的男孩的名字。我们望着他弓着身子,缓缓爬上慢坡,走进屋子,出来时两手空空,直到他跑到湖边,我们才看到他屁股后面的裤兜里插着一个透明的玻璃瓶,骄傲地一闪亮一闪亮。老刁没让筏子靠岸,而是将竹竿向儿子一推,海天一伸手抄住了,像老刁那样,竹竿一点地,唰地跳上了筏子。筏子剧烈晃动着,有人差点掉进水里,胆小一点的尖声乱叫。
“花生没了。”老刁笑着说,“今天喝酒!”咚一声揪掉瓶塞,浓白惨烈的酒气弥散开。我们围坐成一圈,轮流接过酒瓶。孙宝扭头避让着,猫头抢过酒瓶,咕咚灌了一大口,脸色陡变,望着我们,眼睛潮红,憋了一口气,脖子梗了梗,眼角浸出泪水。三皮只抿了一小口,猛一转身吐了,狗一样伸出舌头,用指头弹拨着。我们笑了起来,海天厚厚的肩膀一抖一抖,老刁啪啪拍响大腿。整个下午,我们任由筏子在湖面漂荡。我们看到牛马立在湖边,仰着脑袋,吃惊地望着我们。牛羊越来越小,我们的笑声越来越响亮。
没想到老刁和他的儿子海天竟然有如此好酒量。老刁猛地立起酒瓶,喉结像一只小老鼠一上一下,酒冒着泡儿,汩汩往下落,好半天,老刁才猛然翻过酒瓶,晃晃脑袋,悠长地叹了一口气,抹抹嘴角的硬胡楂儿,摇摇残酒,递给海天,站起来,突然一声长啸,震得四周的大山微微颤抖。海天瞥一眼老刁,嘴角露出一丝笑,垂着头,羞涩地抿起烈酒,一小口一小口,酒瓶很快就见了底。他两手软软地耷在膝盖上,仰起酡红的脑袋,望着父亲,眼睛湿漉漉的。
我们被他们父子吓到了。
……
鱼王
鹰王
豺
甫跃辉的作品,每句都“实”,全篇又很“虚”,他的路数独特。他有与众不同的经历:云南大山中的成长,上海大世界的求学,乡土的滋养,名著的熏陶,这些都能在他的作品中找到踪迹。
——王蒙
甫跃辉是最近几年出现的较有才华的青年作家之一,云南是我们共同的家乡。他的写作在神奇的想象中虚构了一个似是而非的世界,这个世界不是基于现实,因为现实已经在无休无止的日新月异中枯竭,日益乏味。他与对现实充满期待的前辈作家不同,他在想象中创造了一个忧郁的乌托邦。这是未来写作的趋势吗?
——于坚
甫跃辉的小说充溢着大自然生猛鲜烈的气息,是人与万千生灵交织过往的一曲豪浩歌。他将数字时代四散飞扬的化纤尘埃扫除净尽,然后在肥沃的泥土上栽种出自己心爱的铃兰。他讲述的鱼王与鹰王的传奇,令人心向往之,过目不忘!
——张炜
浓郁的远方,温暖的意味,特有的情感暗示,亲切,柔软,升华,产生一种光亮,引动读者的共鸣。
——金宇澄
甫跃辉的小说是慢的、笨的,对生活描摹过于细腻,情节推进节奏缓慢,但耐心读下去,你的心趴下来,会痛,会流出汁水。
——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