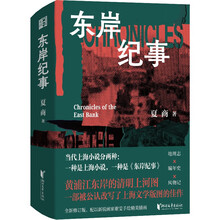01 所谓希望
打开衣柜准备找出门的衣服前,我回头看了一眼床头柜上的小闹钟。闹钟屏幕右上角显示着23度一一为了避免秋冬季节情绪低落,我没事儿找事儿地把温度单位调成了华氏度。至少数字上看着比较暖和。
这种呆办法也只有宅在家里的时候能管点儿用。
按一个按钮,23华氏度立刻变成了零下5摄氏度,看来今天还得穿羽绒外套。换了衣服和鞋拎起包站在门口默念一遍:手机、钱包、钥匙、人。确认全都带了这才锁门下楼。
楼道一侧带护栏的落地玻璃窗开着一扇,透进灰尘味浓郁的冷空气。
每当宅过几天再出门,扑面而来的新鲜感可不是空气质量能扼杀的。长长的楼道一侧依次排列着紧闭的门,大概是因为我从不在上下班时出门,住了一年多都还跟邻居们不熟。靠近电梯那家夏天总是开着大门,隔着挂满灰尘的纱门传出小孩儿的哭闹声、做饭的味道、灰白的灯光、电视的嘈杂声……过完中秋他们家也终于关门了,让习惯了这些动静的我觉得天一冷楼道也单调了许多。
电梯间很空。等电梯的时候,我习惯性地抬头去看墙上的电表,对应我家的那一条窄窄的显示屏上还有三位数字。这倒是挺让人安心,至少短期内不用担心正洗着澡忽然断电。以前总认为囤积生活物品和水电煤气是焦虑的表现,一个人住了一年多才明白过来:乐意囤积的人往往不会焦虑;真正不省心的是像我这种坚持任何东西每次都只买一定量的宅人,如果不借规律的购物行为来保持出门频率,恐怕总有一天要宅在家里长出蘑菇来。
不过我今天不是出去购物的。
我约了人。
什么?男朋友?难道我像是有男朋友的样子吗……
“你这么爷们儿,要男朋友千吗用啊?”李陸毫不客气地一脚松开离合器,车子抖抖索索地发动起来,扑哧扑哧地排着尾气从小区门口上路了。
我就差没用意念把自己变成一块橡皮糖,好稳稳当当地粘在座位上。
虽然早就听他科普过如何租一辆最适合跟踪的车,但我还是忍不住逮着机会就吐槽:“我说你又租这么个‘危车’,就不怕它半路散架?”
“那我下回开辆阿斯顿马丁你看行吗?”他慢条斯理地故作正经道,“就上回那。07电影里在空中翻了好几圈儿(向车。”
他说的是我们几天前在一家小咖啡厅里一起看的《皇家赌场》。
那是我第一次跟着他盯梢。他要盯的一对男女在咖啡厅里坐了整整一下午,我们看完两个半小时的电影还不得不坐在原地回味了一个多小时。
想想邦德那辆阿斯顿马丁,再看看我们屁股下脏兮兮的皮坐垫,我不由得感叹:“邦德开的是改装过的DB5“,惦记惦记就行了,咱们是摸不到的。”
“你说你一姑娘家对车那么感兴趣千什么?”他边说边抬脚加速,伸手拉挡杆,此刻车很淡定,一点儿也没抖。
“买不起还不许惦记啊?”
“你是惦记车呢还是階记车里的人?”
“克雷格叔‘本来就是我们宅女的男神好吗?那大长腿和天然美瞳,看一眼就能把人美哭了。”我不自觉地推了推眼镜。近视没什么大不了的,鼻梁不高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近视加鼻梁不高就有点儿悲剧了:每隔几分钟都要手动推一推镜框,即使它好好地架着没有往下掉,脸也能逼真地感受到一种摇摇欲坠的错觉。
李惟不以为然地问:“你想要他的电话号码吗?”
“你有?”
“你认为呢?”
“当然没有。”
“还好,这说明你的脑子暂时还正常。”
“……你滚开。”
我们都笑起来。
认识差不多半个月了,这还是我们头一回像朋友一样说笑。倒不是因为他不爱跟人说话,而是我在家宅得太久,已经不太善于跟别人打交道,只有在某些毫无戒备的放松时刻才能正常发挥一一似乎今天状态还不错。
李惟是个私家侦探,我是从若千条千姿百态的网络搜索结果中找到他们侦探社的。
他坚称他的工作和我们小姑娘幻想的不一样,而我试图说服他我理解捉奸也是一份维护社会和谐的高尚工作。我们俩第一次见面时他一共说了四句话:
l。“请进,你好。”
2“啊?开玩笑吧你?”
3“别说一周,一天也不行。”
4“再见。”
然而两天后,我坐上了这辆摇摇欲坠的车,完整地体验了我人生中的首次盯梢一一环境一点儿也不艰苦,有茶有松饼,还顺带看了部《。07》。
那天,我们坐在咖啡厅,透过玻璃窗看着那两人出门走向停车位上车离开。李惟收回目光看了我一眼,问:“比你想象中无聊吧?”
“我想象中比这无聊才对。哎,我们现在不用跟了吗?”
“天晚了。我去跟,你回家。”他站起来,抓起外套就这么走了,事先都不带缓冲的。
他刚刚喝绿茶的杯子还摆在桌前,一丝未散尽的热气正从杯里微弱地升起,而人已经不见踪影。看见了吧,这才是货真价实的“一溜烟儿”。
车驶入主路,右转往市郊方向开去。看来今天(內路程不会太短。
跟着盯了两三回梢,今天他难得地带我去找人了。严格来说他已经差不多找到了地址,今天只是亲自去确认而已。
不到半小时,窗外的风景迅速由连绵的建筑过渡到冬天光秃秃的林野。路边的指示牌规律地一个接一个匀速出现,似乎要上高速了,而他似乎仍然没有要从匝道下主路的意思。
“我们快到了吗?这是哪儿?”我问。
他不答话,从方向盘上挪开右手对我一伸。老规矩,在没确定我身上没有任何可以拍照或录音的电子设备之前,他不会讲跟具体工作有关的话题。比如此刻,我只知道跟经济纠纷有关,他是去找一个躲债的。
我麻溜地从包里翻出手机关了交给他。
“哟,今天没带录音笔?”他笑道。
“反正你也不让我录。”
“我好像让你录过不少吧?”
“那是你给我科普的时候,跟具体事件没关系你才让录。”
“工作时间让你跟着本来就不太合适,还敢给你透露调查对象的资料,我就不用千了。”
这倒是真的。之前无论上哪儿盯梢,他都不会让我知道被盯的人叫什么名字、做什么王作、为什么被盯、谁委托他盯。即使让我看到那些陌生人的长相,也绝对不准许我私自拍照。
我推了推鼻梁上的眼镜,答道:“所以我只能白看看,明白。”
“录音笔交出来吧。”他目不斜视,语气平淡得就像在问我吃没吃饭一样。
“我没带。”
“不交出来我可就在这儿把你放下了啊,”他居然像模像样地开始减速,仪表盘上的指针直往下滑,“这儿没公交没地铁,出租车一天也难得有一辆路过,你自己看着办。”
车自从跑稳了之后倒是没再抖过,这会儿该抖的是我才对。
“我真没带,不信你翻我包!”我一把按住座位左侧的安全带扫,以防旁边这位“一溜烟儿先生”迅雷不及掩耳地把我赶下车。
车还在继续减速,他仍然和颜悦色慢条斯理。他语气越真诚,在这荒郊野外就越瘳人:“下了车你就在原地等我,千万别乱跑,我回程经过这里再捎上你。”
仪表盘上的指针滑过了20,还在降。
该死,李惟这货果然拾手打了右转向灯!要么他是真想停车放下我,要么就是专注细节演得逼真。
几十秒后,车停了。
他侧过头一脸无辜地看着我,不再说话,仿佛把车停下来不走的人是我。
我下定决心打死都不下车,比刚出发时更加努力地试图把自己粘在座位上:“跟你说了没带,要撵我下车也还是没带。”
他无奈地抿了抿嘴,一言不发又发动了车子,还顺手打开了收音机。
“喂,你真不信我没带录音笔7”
他不吱声,而是特別欠揍地跟着收音机里的音乐节奏一下一下点头。
车窗外电线杆和树依旧一根一根有节奏地从两侧掠过,口水歌的旋律在耳边绕来绕去,车内狭小的空间让这沉默又聒噪的氛围更加烦人。最讨厌广播电台播这些朗朗上口的歌了,数分钟后我的大脑果然成功地被入侵,思考功能暂时关闭,只有一排带旋律的字幕在脑中循环播放:“你存在——我深深——的——脑海里”……什么叫情不自禁,憋住了没跟着唱就叫情不自禁。不对,是叫自制力。我果然死机了。
他该不是这一路都不再说话了吧?
坚持了一阵子,我终于挺不住了决定投降,伸手从外套兜里掏出那支录音笔,关上再扔进座位前的储物格。
“你怎么知道我一定带录音笔了?”我不甘心地问。
他说得轻松自然:“你右手一直插在兜里,坐进来以后连车门都是用左手关的,还能更明显点儿吗?”
他这人就奇陸在这里:有时候明明挺讨人厌的,可总不会让你产生想抽他的冲动。相反,我现在脑子里塞了个大大的“服”字。
我叹了口气,自觉地換了个话题:“那人特意跑到郊外躲债,你是怎么找到的?”
“这一个比较傻,换了电话卡但没换手机。要吸取教训,姑娘,这就是不好好设置iCloud账户的后果,按一个键就知道手机在哪里了。”
“你居然黑人家的苹果账号?!”我开始琢磨今晚回家就把同步设置改改,否则哪天随便谁随手一黑就能看到我的……生活照。唉,还是算了吧。电脑里连张不能见人的照片都没有,作为成年人我已经无趣到了一定境界。
李惟在一旁坚持既不承认也不负责的原则:“这是你的猜測。未经证实就不是事实。我只说了他做过什么,并没有说我做过什么。”
这倒是,他刚才最关键的一句里根本没有主语。真贼。
好吧,我也不纠结他认不认了。先满足好奇心要紧:“真的假的,找个人这么容易?你是猜到的密码呢还是用什么强制手段登上去的?”
他对我后一个问题充耳不闻,只继续对我进行信息安全教育:“你没看新闻?前段时间CIA局长戴维.彼得雷乌斯的外遇事件,就是被一封邮件揭发出来的。別小看了现在的通信方式,间谍头子都是这么栽的。”
我被噎得停了两秒才接上话茬儿:“千你们这行的都这么多疑?”
“千你们那行的都这么好奇?”他反问。
这真是个好问题。
事实上,我向来不知道我的同行每天都在做些什么。仿佛他们全都有永不枯竭的天分,只需要偶尔停下脚步来捕捉脑海里讲不完的故事。
曾有一位很著名的同行前辈说过:出名要趁早。
我信了。
直到过了好几年我才意识到:她只说了出名要趁早,却没说趁早出名之后该怎么办。
有人能一次又一次刷新自己的纪录,而有些人却泯没于众人。很不幸,我属于后者。都说长江后浪推前浪,我成为前浪时年纪还小,以致根本没明白自己这些年来是如何渐渐死在沙滩上的。
如果非要用一句话总结我开始得过早的职业经历,只有“生得耀眼,夕匕得十脆”
我不想就这样结束。
我需要一个好故事,一个能咸鱼翻身的好故事。
而李惟一一我旁边这个敏锐、多疑、其貌不扬的私家侦探——是我最后的希望。纵然希望渺茫,怎么说也聊胜于无。
伴随着这车上下颠簸的节奏,我转过头凝视坐在驾驶位上的李。个子不高,下巴上留着青灰的胡楂儿,领子磨得有点儿白的旧衬衫,式保守的羽绒外套,手腕上有些年代了的登山表,搁在杯架里那只盖子磨损得不轻的保温杯……他就是我最后的希望?
横看竖看都有种死马权当活马医的悲壮。
再低头看看自己:两年前买的旧手袋、久未保养的靴子、不讲究款式的宽大羽绒服,整个人都显露出长期缺乏社交生活的疲态。哦,另了那支旱该进博物馆的录音笔,它现在正躺在这辆同样该退休的旧捷达的储物格里。
车窗外一片前不见来处后不见去路的荒野,真像我现在的生活。
见鬼,我到底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
这一切要从两个月前出现在我眼前的一张名片说起。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