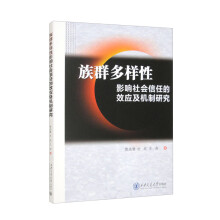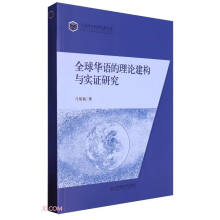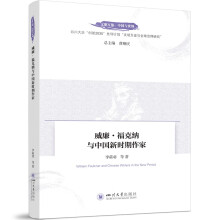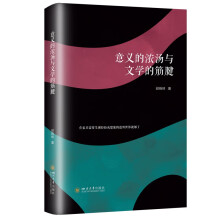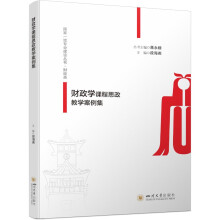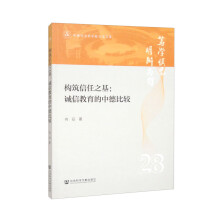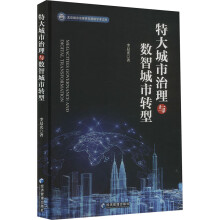感谢我的学生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朱海燕、马海英编辑以及她们的同事的帮助,《政治、经济与福利》的中文译稿终于和大家见面了。对我来说,这是一个长期的心愿,但苦于忙忙碌碌的教学、研究和事务性工作,翻译一直没有推进。我常常诧异,为什么这样一本对人类福祉有如此重要意义的政治经济学著作没有得到诺贝尔和平奖评奖机构或者更广泛的学术社会的关注。作者们自己谦虚地说书中的很多思想来自其他作者的贡献,但书中对经典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分析和评论,确是出于他们自己的经验、认知和创意,特别是他们提到的面对面的熟人小组社会对人民生活质量和幸福感以及性格塑造的重要性,与2009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艾莉诺?奥斯特罗姆的小社区公民自治和公共池塘资源管理的设计原则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宏大的历史叙事和对工具性细节的关注,更是令人高山仰止。
我一直认为,这是一本十分重要的著作。在中国跻身有影响力的世界大国行列、开始探索引领人类文明发展的关键时期,我们急切地希望本书早日问世,给大家一些讨论和思考的提示。 国家的发展,不应单纯从经济增长、市场行为、意识形态的角度衡量,而是要从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综合思考。 当然,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是让这些参与翻译的学生认真反复阅读本书,其中有好几位都将所学的理论用到了他们的硕士或者博士学位论文之中。
这本书的第一稿在1953年出版,正值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对抗的时期。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本书在当时并没有获
得它应有的社会影响力和历史地位。 我在20世纪80年代末读研究生时阅读了这本著作,但在当时没有领悟到它的一些思想与我国现阶段的深化改革会有如此密切的相关性。所以,在这个时候推出本书,希望“犹未为晚”。
改革开放后,我们这一代学人负笈海外,开始系统地接触和阅读国外的社会科学和政治经济学原著,并认真思考为什么当时认为已经“垂死”的资本主义依然生机勃勃、经济发达。但读完这本书,才真切地感受到,社会发展的过程,比简单的意识形态的划分要更加复杂和多维。从社会发展的目标来说,自由资本主义提出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与马克思主义提出的“追求全人类的解放、让人类社会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伟大理想”并不矛盾。但在具体的社会运行过程中,两大阵营的对峙,核心焦点在于社会治理的方法的不同。 中国的改革,增加了市场经济的自由度,也加大了国企和政府用人路径和策略的自由度。更宽松的人才制度,给大量的人力资源创造了发挥能力的环境和机会,推动了中国经济社会的高度增长和发展。
这本书的思想,建立在对民主社会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的理论思考和实践结果进行比较的基础之上,有几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对我们反思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重新审视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在改革开放初步成功后继续探索前行的方法,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第一,达尔和林德布洛姆两位作者相信理性的作用。他们提到,历史显示,现代人运用理性的努力,反映在他们的三大知识运动之中。第一次知识运动是文艺复兴运动。巴黎大学和牛津大学的学者们从古希腊的故纸堆里发现了人类的古老信仰――对理性的崇拜,对自身美和力量的崇拜,对人们能通过自身的观察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认识世界并进而控制、改造世界的信心。东罗马的灭亡又使他们留下的古希腊古罗马文献回归到意大利。这些人类对自己的信心带来了人文思想的兴起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形成了改造世界的巨大力量。第二次知识运动当属“自由资本主义运动”。 在这一运动的推动下,人们开始用市场的方法控制社会经济的运行,用民主选举的方法来控制和平衡社会力量,同样取得了经济和社会的大发展。但是,当市场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出现大经济财团控制选举和政治决策时,这种平衡就被打破。当政治和社会力量向财力雄厚的大财团倾斜时,政治失衡、社会失衡就会发生,引起难以调和的阶级矛盾,成为暴力造反的铺垫。这个倾向,在21世纪也愈来愈明显。 英国作家皮克迪的《21世纪资本论》其实是对这一理论的最好注解。作者收集的数据显示,除了战争的时期,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一直越来越大。这个倾向,并不是后来的社会学家波兰尼的 “双向运动” 理论可以很好解释的。因此,根据达尔和林德布洛姆的推论,第三次的知识运动应该是“民主社会主义”,既包含社会主义也包含民主主义,缺一不可。在这里,人们将经济事务也政府化了,同时用理性来控制经济和政治这两个过程。第三次知识运动在二战以后事实上已经开始了。但是,在理论与实践的完整结合方面,并没有做得完善和令人满意。在这里,我特别要提到的是,达尔和林德布洛姆两位作者认为的“历史终结点”并不是近40年后的美籍日裔学者福山提出的“现代自由资本主义”,它至少是“民主社会
主义”,是超越自由资本主义的“历史的终结”。
说到这里,或许有人会想,中国为什么没有文艺复兴或者启蒙运动?事实上,在中国,这个过程也存在。开始的时候也是由外力导致,然后开始自我寻根。鸦片战争使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推动了变革,如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民主革命、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人民在奋勇抗争中实现了民族独立,建立了新中国。同时,甲骨文和莫高窟的发现,让我们重拾对悠久文明和伟大文化传承的信心和希望。 可以说,东西方文明的不断碰撞和生生不息,其实都有着各自对文化之根的眷恋这一相似的内在逻辑,这是理性之外的感性力量――或者说,一种超理性力量的作用,是“心”之力。
第二,本书直接指出了“现代自由资本主义国家理论”的局限性,对西方主流观点提出了系统性的批判和发展。作者提到,在决策方面,经典自由资本主义强调每一个人的权利,把公共决策放在为私利讨价还价、少数服从多数的票决基础上,没有能力用理性来对待现代社会出现的新的集体性问题,如环境污染问题等。它们的国家能力注定会在这些方面表现出不足,而社会主义国家则需要思考如何用好公权的问题。作者认为,“在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计划经济还是自由市场、管制还是放任自由等传统的选择之外,还存在其他意义更深远的选择”。传统上看似“简单而又重要的选择” 其实 “并不那么简单”,因为经济组织所遇到的棘手问题只能通过更加谨慎地关注技术性细节才能得到解决。并且,一些所谓的重要选择其实没有那么重要。他们认为,美国的经济是过度私有化的,美国人对私有制有着教条式的偏好,因为在农业社会时期,私人所有和控制的经济组织在效率和民主方面有合理的社会基础,但这种偏好只是一种信仰,并不是公众在理性计算了它的相对优势后得出的结果。
本书认为人类文明社会的终极目标有三:将自由的可能延伸到极致,接受每一个人在追求自由过程中对平等的要求,通过人的理性控制能力保障拓展自由、捍卫平等过程的不断进步。具体说来,这个终极目标可以有多维度的表达:生命的存在、心理愉悦感、情感、尊重、自我、权利、技能、知识、名声、审美、激励、创新力。这些终极目标可以通过自由、理性、民主、主观平等、安全、进步和适当的包容性来实现。但是,人们在讨论终极目标时,往往只注重限制人发展的某一部分的环境和条件,却忽略了首先解决贫困、经济不安全、分配不公等问题才是提高人类福祉的最基本的条件。并且,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法,对于人类最后达到这样的终极目标,也有决定性的意义。
第三,这是一本关于自由主义的著作。如果我们记住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提到的“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人类社会奋斗目标,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宏大而艰巨的任务,是人类的最高追求。但是,自由不是绝对的,在不同的社会认识情况下,人们对自由的理解是不同的,它受制于自然环境、物质条件、内心诉求、他人诉求等等。不同的国家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有为大众所认可的、共识性的自由观念。作者指出,完全自由的社会是不存在的,“一个人的自由或许就是另一个人的奴役”。对不同的群体来说,自由会鼓励和禁止不同的行为,因为社会存在于相互的控制之中。追求自由的重点在于通过理性选择追求进步,克服对自由的阻碍。作者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对社会本质的认识超越了经典资本主义:一是意识到价格体系作为一种社会调节机制的不足,意识到这一机制带来的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和对集体公益的忽略。 二是意识到社会生活的整个过程并不能没有控制,不论是市场、技术、文化还是公共事务,没有合法的控制和理性行为,这些就不可能成功。三是市场化的竞争控制手段需要有辅助性的科层结构控制手段来弥补,否则纯价格体系的运作不可能成功。四是收入分配的合理性和公共政策的调节力的重要性。他认为,自由资本主义之所以有所成就,即在于对这些问题有相当的共识。对于我们来说,深刻理解自由的意义,就不会惧怕自由这一提法,而可以更好地表述自己,与世界文明对话。
作者花费了很多篇幅讨论理性计算和社会过程,认为理性计算是达到自由、民主、主观平等、安全和社会进步必不可少的手段。
作者认为,有四种实现控制的社会过程:价格体系(市场机制)、科层制、多头政治和讨价还价。在价格体系中,人们通过计算交换的利益来互相控制;在科层制中,领导者控制非领导者;在民主多元体系中,非领导者控制领导者;而在讨价还价体系(寡头体系)中,领导者之间相互控制和制衡。
达尔和林德布洛姆用相当的篇幅讨论了社会控制的机制。他们认为社会上存在四种基本的控制技术:自发性领域控制、操纵性领域控制、命令、相互控制。自发性领域控制比较随意,它是对某一发生的事情的即兴反应,没有事先的计划。比如遭受欺压后的即兴反抗,挨打后的还击,价格提高后主动减少购买行为,等等。这种反应对事物的发展有控制作用。这种反应的机制也往往深藏于文化和传统之中。操纵性领域控制通过喜好、尊重、情感、愉悦或者愉悦的剥夺、同情、恐吓、鼓励、友谊等关系来影响被影响主体的行为。金钱和权利也可以用来操纵。命令存在于特定的训练条件下,比如威权秩序的建立,科层结构的存在,发令者对执行者的命令。这种控制机制也需要事先的制度性培养。相互控制指的是相互控制的多个主体之间的互动,各自从控制中得到好处和平衡。当然,这些控制机制有直接作用的、间接作用的,也有需要一定的条件环境和沟通媒介才能完成的。
对于达尔和林德布洛姆来说,社会行动中的控制无所不在。在生产过程中叫技术,在国家发展中叫计划,在市场过程中叫交换,在社会行为中叫文化。这些社会过程时时刻刻反映着人类的理性,这些过程的良好协调,才是达到社会目标的关键所在。
第四,协调,就是行政手段的合理使用。本书的核心要点也在于提出要注重协调和行使行政权力的细节。在20世纪90年代版的前言中,达尔和林德布洛姆写道:“我们在 20多年前(1953 年)就写了这本书,批评当时盛行的观点――认为只要有几个聪明的人帮助大家在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管制还是放任自由之间进行一个简单选择,就可以应对一切问题。到 1991年,苏联解体了,但资本主义的方法也开始受到更大的挑战。 虽然有人认为过去一个世纪,自由资本主义更有利于追求自由、效率、正义、平等、安全和进步,但事实上,自由资本主义中违反这些神圣价值的例子也不胜枚举。我们这本书的最重要的理念是,看起来简单的道路,其实是不可能简单的。现代经济组织给我们带来的问题只能通过不辞辛劳的对技术细节的关注才能得到解决。”
现代国家的累进制税收政策、福利政策、劳工保护政策、反垄断政策、中小企业保护政策、市场补贴政策、国家标准政策、国家工程政策、教育政策等等全面介入社会,核心关注点从产权归属转移到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生命、权利、平等、公正、自由、尊严和幸福感上。如何用好公共政策,推动良性国家治理,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新时代中国人民新的追求。
需要注意的是,本书作者所讨论和描述的“资本主义”和“私有制”、“社会主义”和“公有制”,指的是20世纪上半叶的经典资本主义和传统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本书于1953年出版,所列举的大量例子也是那个年代的例子,与后来经过不断改革的现代资本主义(如肯尼迪的“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什么,只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什么”的资本主义、约翰逊“族裔、男女平权,保障社会福利” 的资本主义,以及“奥巴马全民医疗保障”的现代资本主义)和我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以人民为中心、深化改革开放、走向世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十分巨大的区别,因此,不应该进行简单类比或概念套用。但达尔和林德布洛姆提出的要用好社会控制技术、追求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通过辛勤的努力做好国家治理的细节工作等重要的思考和分析,对于我们理解世界、走向人类文明的思想前沿,有不少有益的启示和重要的参考价值。
本书的翻译工作在2010年就开始了,几经易稿,其间多次开讨论会,多次因译者中英文水平问题换人,学生们繁忙的学习和论文写作多次打断了翻译的进程。但团队中的部分成员锲而不舍,直到毕业和出国后还依然执着地参与阅读、翻译和校对。虽然有的学生翻译的章节被大幅修改和重译,但他们的功劳依然应该得到认可。本书的翻译工作基于译者对理论的了解,因此理解起来不会太偏,但细节上也许难以尽如人意。本书作者的思考方式是西式的,因而遣词造句也与中文差异较大,这使得我们在信达雅方面难以平衡。另外,我还在主持翻译工作时加上了“一定要简明易懂”的原则,当句子很长很晦涩时,更注重意译,不强调形式和结构。这样的好处是,至少这首先是一本能看懂的译著。
参加本书翻译的学生有崔亚杰、邢贺超、宋学增、黄衔鸣、张腾、于溯阳、苗爱民、刘洋、杨明洋等等。特别是于溯阳,先后做了大量的统稿甚至重译工作,张腾、路畅、薛金刚进行了多次的阅读和校对。我自己也校对和重译了许多有误解和不准确的地方,并通读和修改了整个译稿。是大家的努力,使得本书的问世成为可能,给读者奉献了这场思想的盛宴。希望随着时间的检验,这本书的意义和价值可以被更多人所发现和认可,让更多的学人得到启发。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