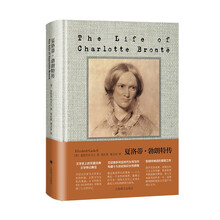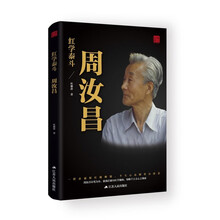佛说:芸芸众生,如鱼过江,谁又能为谁停留摆尾。然不经意问,你我能为彼此驻步,此乃冥冥天意。纵然今生未能厮守终身,相伴经年,亦是心足。
尘世辗转,人生如梦。曾经年少轻狂,执着地行遍万水千山,望遍天涯孤月,那是一个女子——三毛。一个四处流浪摆弄文字的怪女子。她的故乡,在远方。因此,她将永无休止地在追寻。
这世间更多的女子借着一柳、一树、一把丝绸伞,杨柳岸边,吟风弄花,如诗如画演绎婉转的情长梦短,似水流年。
而三毛却在浩瀚凄艳的沙漠中留下了一个倔强的背影,在异域他乡把万水千山踏遍,留下了一个个让世人无法模拟的足印。一次次,三毛如此固执地、在撒哈拉的沙漠里风轻云淡地告别她的情、她的爱、她的怀恋,轻轻地飘过,随着云彩一起流浪,坠落又腾空。
人生似梦,曾经沧海,一樽还酹江月。任凭风吹雨打,看庭前花开花落,任天上云卷云舒,沧桑变化,心中的那梦就是永不凋落的花,沉淀,升华,成像,散发迤逦的光,普耀。
这世间,任何精彩和传奇,总会有个开始,有个追寻。
如今,在那嘉陵江畔正上演着一段传奇。
人世烟雨红尘,吹落了一年年梨花似雪。嘉陵江畔的重庆,是一座美丽的城市,寒暑暗转,迷雾朦胧,繁华而又安然,没有什么倾国倾城的爱恋,亦没有凄风苦雨的成全。
战争年代非常残酷,让生活的环境也透着悲伤的味道。1937年,国民党政府在日本战火的蔓延下,迁移到了重庆。这座宁静的雾都山城,却成了中国战时的陪都。
重庆一下子就热闹了起来,集中了形形色色的、来自四面八方的异乡人,军人。首都在前方抗战,背后的山城还是车水马龙、夜夜笙歌,前方百万横尸的血还没有流到这里,还是一片纯净的自然。
流离失所成为那个年代的咏叹调,战火逼迫之下,带着疲乏和寄望,陈嗣庆一家流离至此,如一缕浮萍,无奈自安然。
在1943年3月26日,一个小女孩出生了,她就是三毛,出生在一个名叫黄角桠的地方,那是一块出尽才女和才子的土地。她是光阴的使者,又仿佛一个时代的浮起,一切只是为了成全她这样一个绝艳的传奇。
如血的战争岁月,诞生了如花的幼小生命,带着淡淡的清香,飘在了陈家的庭院之中。一双冷眼,热望尘世,化做心泪如雨。她出生之时,正有淡红色的曙光,透过氤氲的薄雾,把上帝和平的福音,透过山峦重雾传递过来,敲响了生命的那口钟。
至美之景,诗意而苍凉,为这个女婴的到来渲染了特殊的底色。也许只是偶然,也许真是个奇迹,三毛在这个时候出生了。
人之初性本善,婴儿是世间最纯净的了。婴儿是无欲无求的,但他终将渐渐地载起梦想,载起期望,载起人生,最后载起一个沉重的壳,再也不能翱翔,只能在这个满是人的世界,匍匐前行。
饱受颠沛流离之苦的陈嗣庆,对这个初来尘世的女婴寄予了一个知识分子和基督徒的理想,他为孩子取名叫“陈懋平”。
“懋”字,是家谱上属于她那一代的排行;而在那样一个特殊的年代,“平”正是和平、平安之意,也是一个文人无力于时势只能寄托于文字的懦弱。耶稣教徒的祈祷,在这个孩子的身上赋予了和平的使命,也是最朴素而美好的愿景。
父母都希望子女一生平平安安,不求大富大贵,只愿平淡幸福到老。三毛没有大富大贵,幸福只是敲开了窗,还没有来得及入内,就又跑开了。
三毛的命运注定是多舛的,小时候的自闭性格让父母忧愁,几次的自杀让父母伤心白头,父母含辛茹苦把她养大,她又远赴异国他乡,寻找别的安详。最后竟还是无恋于世,引颈自杀。
小时候的三毛很聪明,很早就学会说话、走路,又学会了看书、写字。
三毛长到三岁时开始学习写名字,却总也写不好笔画复杂的“懋”字。小孩子图省事,就把“懋”这个字跳过去。
陈嗣庆只得顺水推舟,给她改名叫“陈平”。这是三毛的第二个名字,也是她的第一个笔名,在她十七岁的时候,被大众所知。其他几个孩子跟着沾光,也享受了这个待遇。这样三毛在三岁的时候就个性了一回,隐约露出固执的苗子。
说到名字,“三毛”这个名字是《沙漠中的饭店》里给自己取的笔名,那是她1974年发表的短篇,那个时候她正与荷西幸福地生活,每天的欢乐足够多,哪里会想到后来的那些苦难。起这个名字没有和那个小“三毛”挂什么钩。
三毛只是说,这个名字笔画很好,很是简单。
后来还有人说“三毛”这两个字,是一副卦。三毛是很相信这回事的,如果真的是这样,取这个名字也不无可能。
在那篇文章以前,她一直用“陈平”发表作品。
另外,她还有一个英文名字,叫“ECHO”(艾珂),这是一位希腊女神的名字,没有爱情、充满哀愁,就像三毛满腹的痛苦无法说出口。
1989年,三毛第一次回大陆探亲,那个流传着民谣的故乡。在故乡小沙乡,她告诉记者,她要用一个新笔名,叫“小沙女”,纪念她的故乡。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