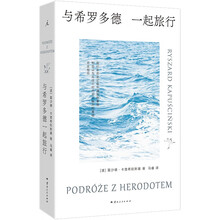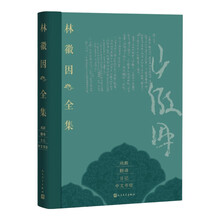《书学探微录》:
为此,他们“分析各种观念,注意观念的隶属关系,建立观念的连锁,不让其中缺少一个环节,使整个连锁有一项颠扑不破的定理或是大家熟悉的一组经验作根据,津津有味的铸成所有的环节,把它们结合,加多,考验,惟一的动机是要这些环节越多越好,越紧密越好:这是希腊人的智力的特长”。并且对于这类的思想之旅,“他们不因长途迂回而感到厌烦;他们喜欢行猎不亚于行猎的收获,喜欢旅途不亚于喜欢到达终点。在希腊人身上,穷根究底的推理家成分超过玄学家和博学家的成分……希腊是无事生非的强辩家,雄辩学教师和诡辩家的发源地”。甚至说“真理是他们在行猎中间常常捉到的野禽;但从他们推理的方式上看,他们虽不明言,实际是爱行猎甚于收获,爱行猎的技巧,机智,迂回,冲刺,以及在猎人的幻想中与神经上引起的行动自由与轰轰烈烈的感觉”。
我们当然不是要把丹纳对希腊人的分析判断,简单生硬地“套”在中国人身上。这里只是试图说明,有一类人对逻辑思维的爱好和热情超过了形象思维,他们视抽象艰深的“理”同样是有趣的;并且这一现象不独在希腊为然,也不独在“纯粹”的理论研究中为然。
第三,从“理”自身看,总的说必须是独到的、新颖的、深刻的。马克思为讨论剧本《弗兰茨·冯·济金根》致拉萨尔的信中,认为写历史剧要“能够在更高得多的程度上用最朴素的形式把最现代的思想表现出来”。对说理诗来说,这一观点同样适用。《散宜生诗》所以取得很高的成就,“新题材更新思想,新语言兼新感情”是重要原因。这也对创作主体的思想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