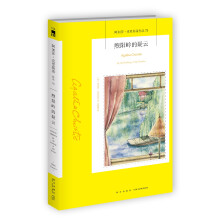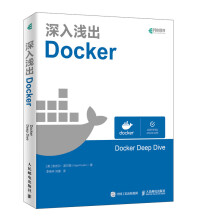如果结合前文分析的陆川导演特质中,那种介于第五代和第六代中间的特殊气质来看本片的话,《南京!南京!》作为一个文本的价值,还在于它提供了后续创作者对于南京大屠杀的一个例证性的引用。例如,在此后拍摄的、第五代大导演张艺谋的影片《金陵十三钗》中,就再次出现了《南京!南京!》中曾出现的“妓女救国”的情节。这种互文性也同时常常引起巨大的理念争议。对妓女的态度反映了中国社会现代化伦理观念转型时的矛盾性,而在对拉贝先生的翻译官唐先生的处理上,也同样反映着中国式的伦理价值和西方文明价值体系的冲突。唐先生为了自己家庭的安危出卖了金陵女子学院的“安全区”,使得很多国民党军官士兵们被枪杀,他的行为可不可以被原谅?当陆川谈到历史真实和中国人的世俗现实一面的时候,他面临的是导演的自我逻辑某些时刻是不够自足的,过于强调自我意识的结果,就是他本人的观念不能够有效地统和受众的认知空间,这当然也成为了作者导演的通病,“真实”是否可以被真实地模拟在影像空间之中?在《南京!南京!》的商业体例中,这个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不同于《金陵十三钗》中编剧刘恒、严歌苓等人对于叙事走向的整体性影响,陆川的作品一直是以编导合一的形式出现的,这可能受到了他的父亲、著名编剧陆天明的影响。而这也就使得陆川成为了他的电影的绝对作者。通过编剧、导演和后期剪辑的“三权统一”,陆川的电影就构成了他世界观和价值观的直接表述。在他的影片中,中国的苦难表现在日军叩开教堂大门以后无数难民麻木而安静的面孔上,这些面孔中透露着纯粹弱者的气息,他们怯懦地躲闪着,被动地等待灭亡的命运。他们既表现为慷慨赴义的勇敢妓女和大义凛然的高贵教师,也表现为惊声号叫换取同情的顺子和人道主义救亡百姓的国际友人。可以说,陆川的《南京!南京!》正是包含了当年鲁迅经历的“幻灯片事件”、对待白人的“白求恩印象”,和传统文化中的士大夫精神的杂糅,陆川引起的一波波争议同时显示了中国社会目前价值观及世界观的多元化倾向以及其中的互相倾轧,陆川的作者身份使得他的电影中的“我”永远是他自己,而非应该承担起整个民族灾难的“国民们”。总的说来,他的“作者现象”实际上构筑了中国电影批评史上仅次于,或在某些领域更突出于张艺谋的舆论变化,这其中显现的社会思潮的变化,也将时代与个人紧紧地联系了起来。
四、国族历史的另类追寻:对弥赛亚主义的反思
与其说陆川喜欢标新立异,不如说他往往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中难以自拔。当国人将汉朝追溯为汉民族支配的中华文化兴发之际的时候,陆川却依据他独特的现代主义情怀,将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表现为一个回顾历史仓皇失措的垂暮老人,一个被历史和英雄们裹挟的脆弱的人质。国族历史的书写变成了一部个人史,本来是建国君王充满了传奇色彩的《鸿门宴》,却变成了荒腔走板、令人费解的惊悚剧。而这其中最惊悚的是,太祖刘邦的一生都活在这样的生存焦虑之中不可自拔。这又何尝不是自《寻枪》以来,陆川作品中一贯的主题?
在有些评论者看来,“陆川的故事片创作在风骨上总体是坚决冷峻的硬派风格,但是在主题处理上有时却犹疑不定、暖昧不清,甚至会迷失在众多的细节呈现之中,这种风格与主题之间的矛盾让人难以把握。”①然而,看似复杂的陆川的“电影迷宫”,实际上如果循着陆川本人的自我言说机制,就可以清晰地找到“米诺陶迷宫”的出口。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