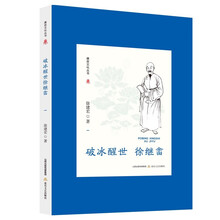直面生命的杂乱
本书讲述的英雄和事业,能够简化归结为两大类:农民起义型和改革建制型。
Kevin?Kelly在他的《失控》一书中,透过生物学视角研究21世纪的社会经济现象。借用他这套妙趣横生的理论,同样可以从生命的角度来观察历史事件,特别是农民起义这类事件。
从陈胜揭竿而起到黄巢、李自成、洪秀全,但凡农民起义运动,开始总有那么一段风生水起的美好时光,英雄领袖们敏锐地觉察到众生渴望的潜流,把握住某种时代脉动,与之产生了共振,很快,他们在麾下聚集起大批人马,势成燎原。在意气风发、豪情万丈之际,如果他们肯冷静下来,回头审视站在身后的人群,就会发现这是一个令人困惑、难以把握的系统。
机械系统的运转是线性的,可预见的因果关系连接着输入和输出;而人群,以及其他社会性动物所形成的“群体”,则是一个活系统,有着自己的生命韵律。
生命通常具有几个基本特征:自我复制、自我管理、自我修复(有限)、适度进化以及局部学习。正是这些特征造就了“群体”活系统的迷人之处:
1.蝴蝶效应。对初始条件非常敏感,短短时间内,细流可以成海,捧土可以成山。
2.随着群体壮大,其中彼此关联的个体所形成的组合数量呈指数增长,从而蕴藏了无数可能性。
3.群体中允许个体有差异和缺陷,个体的缺陷和变异,甚至能引发整体的进化过程。
上述几点在历次农民起义中表现得十分清晰,比如,李自成哪怕是在二次受挫之后,领数十骑进入河南,仍能在当地迅速召集几万人马,一年之后,队伍已达50万人,公元1644年进北京之时,以他为最高领导的大顺军已号称百万。起义军成员多为饥民、流民,个人素质良莠不齐,也不乏投机者,但这个巨大群体不断成长,在吸收了李岩、牛金星等知识分子后,又产生了斗争策略和革命纲领的进化,在最终的狂潮中,摧毁了挺立近300年的明王朝。
但这种活的“群体”同样存在十分明显的缺陷:
1.效率低下。缺乏严密的中央控制,其资源分配高度混乱,冗余设置,重复努力比比皆是。
2.不可控性。没有绝对的权威,起义领袖对起义军的控制经常犹如羊倌牧羊,一旦有变,百万雄师瞬间散了个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3.不可预测性。群体成员间的复杂纷乱的关系,使整个群体的发展命运充满了意外。
4.不可知性。由于很难用线性因果关系来解释系统内部的运转,英雄领袖们尽管多为人中豪杰,面对最后的败亡,也常有“天欲亡我”,“人算不如天算”的喟叹。这里的天,其实就是超越个体理解力的群体运动方式。
5.非即刻性。启动一个复杂系统,达到各层面的协调一致,通常需要更多的时间。起义军领袖经常会在某一时刻,骇然发现已经无法驱动自己亲手建立起的庞然大物。
历史上很多稳固的王朝就是由农民起义发展而来的,比如汉朝、明朝,能否暂时克服这些系统性缺陷,能否适时引入更具可控性的机械系统,就是成王败寇的分水岭。这需要强大的智力和眼光,也需要那么一点好运气。
人们常说的结构与制度,则更多地具有机械系统的特征,这个话题自然地把我们的目光引向另一类英雄,比如王莽和杨广;项羽则是一个特殊的例子,他的人生和事业,与秦末农民起义大潮密不可分,同时也与制度变迁引起的心理不适有着深层的关系。
制度的领先,回归与滞后
关于制度,我们的祖先曾经进行过一场长达500年的大讨论,这就是发生在春秋战国的“百家争鸣”。那个群星璀璨的时代过去之后,真正进入各王朝政治重点实践的,并引起广泛争论的,其实只剩两家,即儒家和法家,对应两条道路,即王道和霸道(最初作“伯道”)。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初。
儒家王道如日,高举张扬,一直是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法家霸道如月,明亮度虽不能与前者相抗衡,却一直没有停止发挥它的深刻影响力,对人间潮汐的控制经常更甚于日。在确定儒学至高地位的西汉,宣帝就曾这么一脸严肃地教育过他的太子——宣帝作色曰:“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令,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安足委任?”
儒家,何曾真正独尊?而彻底回归王道,也就成了2000年来儒者的一贯愿望。如果说秦末项羽的行动更多是受到恢复故国的情感支配,而王莽则是一个高调而自觉的王道回归者。
有趣的是,人们对不确定性的恐惧,不仅表现在新生事物立足和发展常面临的重重阻力,怀旧复古之路同样充满艰辛苦痛。
乞灵于古制未能疗救时疾,王莽的失败在今天看来有些理所当然的味道。600多年后,隋炀帝杨广,以其雄才大略,一扫东晋南北朝的虚浮玄风,重新扶正儒家,首创科举。
科举取士是一项影响极为深远的创新制度,虽因触动门阀大族的政治利益,导致杨广本人的悲剧,但儒学借此机会,扎进每一个渴求出仕的民间才俊心中,从此根深叶茂,在之后的1500多年中,牢牢占据主流意识形态地位。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