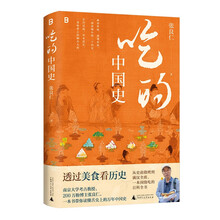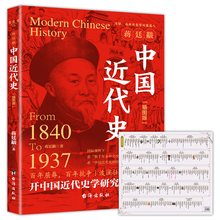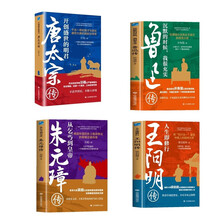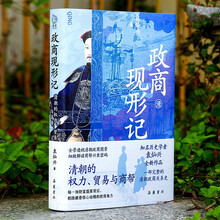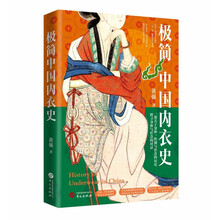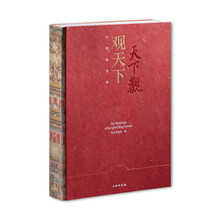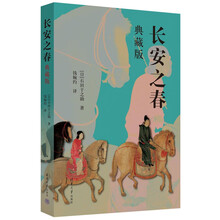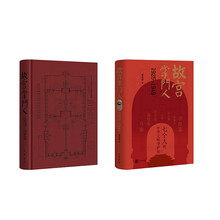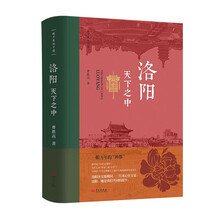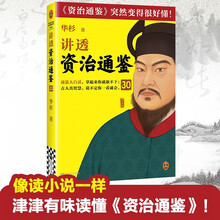二、"老大"的幸福
履新后的袁总统高兴劲还没过,孙中山就公布了《临时约法》。
按照孙先生的宏伟蓝图,中华民国要经历军法之治、约法之治、宪法之治三个阶段。
其中,军法阶段3年,约法阶段6年,然后才进入宪法阶段。
可形势的发展实在出乎意料,当"统一的共和国"像一个早产儿呱呱坠地后,中华民国也跑步进入了约法时代。
3月8日,经过32天加班加点地紧张工作,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了由宋教仁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11日,由孙中山正式公布。
我们很难想象袁总统看到《临时约法》后的心情。
孙中山认为:袁世凯是北洋军的统帅,北洋军曾和革命军在汉阳开战,明明就是反对共和,现在虽嘴上说服从民国,但谁知道心里是咋想的。所以,要有一部约法来"使之服从,并为服从民国之证据"。
不过,袁世凯在短暂的"不爽"后,慢慢镇定下来,用他自己的方式,逐渐摆脱了套在身上的"枷锁"。
对此,当时著名的新闻记者黄远庸看得很准,他在《遁甲术专门之袁总统》一文中指出:
《临时约法》颁定以后,排袁者谓足以钳制专擅……其实雄才大略之袁公。四通八达,绰绰乎游刃有余,受任未及期年,而大权一一在握,约法上之种种限制之不足以羁縻袁公,犹之吾国小说家所言习遁甲术者,虽身受缚勒,而先生指天画地念念有词,周身绳索蜿蜒尽解,比真钳袁君所不及料……无论有何法律,而袁总统必欣以遁甲法地遁。
这部为袁大总统"量身定做"的《临时约法》共7章56条,在《附则》庄重声明:"宪法未实施以前,本约法效力与宪法等。"
其中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主权属于全体国民,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有请愿于议会之权,有陈诉于行政官署之权,对于官吏违法损害权利之行为有陈诉于平政院之权。
这些都没啥说的,毕竟是民国了,共和了,国民当家做主了。
当然,《临时约法》最实质性的内容是国家权力的分配,"中华民国以参议院(采用一院制,没有众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法院行使其统治权"。其中,最核心的是关于立法权与行政权(也就是参议院和大总统职权)分立的规定。
由此,在几年的时间里,中国政治舞台围绕这个焦点,生旦净末丑,狮子老虎狗,轮番上台,演出了一幕幕的喜剧、闹剧和悲剧。
《临时约法》规定: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统率全国海陆军队。但是,《临时约法》白纸黑字还写着:临时大总统制定官制官规,任命国务员及外交大使、公使,对外宣战、媾和、缔结条约等等,均须提交参议院议决同意。
这还不算,作为立法机关和行政监督机关,参议院可以自行集会、开会、闭会,自行制定参议院法,选举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受理人民请愿,质问行政人员,咨请政府查办官吏纳贿违法事件,决定一切法律和政府的预算决算、税法币制、公债募集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
临时大总统如否认议院的议案可咨请复议,但多数参议员仍执前议则总统否认无效。如参议院认为临时大总统有谋叛行为或认为国务员失职或违法时均可弹劾。国务员受参议院弹劾后由大总统免职,大总统受参议院弹劾后由最高法院组织特别法庭审判……
不难看出,《临时约法》虽然还不完备,但基本构成了实行"三权分立"的法律基础。
毛主席曾说:"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较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
不过,"好东东"在某些人眼里却成了"恶婆婆"。因为,它把堂堂的大总统变成了逆来顺受的"小媳妇"。
在当时,中华民国的真正权力掌握在参议院手中,参议院才是中国的"老大",而非袁大总统。
正因为如此,那时的孙中山还认为:"总统不过是人民公仆,当守宪法,从舆论。文前兹所誓忠于国民者,项城(袁世凯)也不能改。"
可惜,"老大"的幸福没有持续多长时间。
按照《临时约法》和《参议院法》有关规定,参议院由内地各省及内外蒙古、西藏各选派5人,青海选派1人组成。选派方法由各地自行决定(大多为省议员互选),全国应选出参议员126人,实际只选出118人,经常出席约70~100人左右。
这样,原以同盟会会员为主的南京临时参议院已不能适应形势的需要,于4月8日起休会半个月,迁往北京。
随后,由各省议会(原咨议局)选举出的新参议员陆续集结北京。
按著名学者朱宗震先生的分析:"他们大体上在30岁左右,年少气盛,情绪容易冲动。多数人在国内外接受过新式教育,属于有思想的新进人物,适应了时代的变化。但这些变化是有限的。前清官僚和有功名的人,占了三分之一左右。留学欧美的人很少,主要是留学日本的比较多,但日本当时还不是一个议会制民主的国家。所以,真正懂点议会民主的人很少。除了官僚以及一直搞政治的人外,主要是教育工作者和自由职业者(律师、记者、医生等)。学习过经济和自然科学的人很少,商人也只是个别的。"
4月29日,位于北京宣武门内象坊桥的参议院(前资政院旧址)内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北京临时参议院在此举行第一次大会,选举吴景濂、汤化龙为正副议长,谷钟秀为全院委员长(审议长),林长民为秘书长。在京文武官员、中外友好都出席了隆重的开院仪式。
袁大总统也来了。
如果说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是个理想主义者,那第二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就是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
袁总统心里对《临时约法》那是相当的"硌硬",对参议院更是又恨又怕。
不过,好汉不吃眼前亏,迫于形势,他还是亲自莅临参议院,以表示对参议院的尊重。
这是袁世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到参议院和议员见面并发表演说。
作为一个政治领袖或公众人物,口语表达能力十分关键。你看西方那些竞选的政客,哪个不是口若悬河、滔滔不绝的。不把选民"忽悠"住了,谁投你票啊。
咱们中国人比较"内敛",讲究"讷于言,敏于行"。
不过,领导们也要经常发表一些讲话。这时,照稿子念的多,自由发挥的少。
大家公认,孙中山的口才很好。
孙先生的粤语演讲录音流传了下来,据当时的革命同志反映,听先生的演讲,那是一种享受。
袁总统的"口条"如何呢?是不是有点"河南梆子味",我们不得而知。
袁总统那天在参议院的演说,主题为"整饬纪纲,修明法度"。
在分析了目前面临的严峻形势(兵事扰攘,四民失业,公私交困,已达极点)后,袁总统就施政方针做了个形象的比喻:造房子先要打好基础,选好工备好料,层层稳固,处处坚实,这样建起的房子才能"历久不敝"。如果为了外观好看,先"虚事粉刷",只怕"墙壁未立",房屋已倒,那损失可就大了。
治理国家和盖房子的道理是一样的,"建设从稳健入手,措置以实事为归"。必须先维持秩序,完固根本,再奋起直追。
话里有话啊。
接着,袁总统从财政收支、外债税赋、工商实业乃至裁军、教育、外交等方面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政见。
老袁摇头晃脑,唾星四溅,讲了足足个把小时。听得台下的参议员们一愣一愣的,连巴掌都拍红了。
大总统很不简单嘛。
可不简单归不简单,在一些原则问题上,年轻的参议员们还是充分发挥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愣是把老袁整得没了脾气。
按照参议院通过的《各部官制通则》议案,国务院各部只设一名次长。
一天,袁总统脑子一热,下令任命自己的亲信张元奇、荣勋为内务部次长。
当总统的任命咨文送到参议院后,议员们不干了:搞什么搞啊,难道总统的咨文能代替法律吗?况且,背着我们"以位置私人之故而增加次长,徒为政府增加闲职",这怎么行呢!
于是,参议院毫不犹疑地回敬了袁总统一记响亮的"耳光":"内务部无须增加次长一人!"
没办法,袁总统只好灰头土脸地撤销了对张元奇的任命。
还有一次就更"过分"了。
从5月11日至7月14日,参议院连续三次咨文袁总统,催收政府预算案。
老袁实在拖不下去,就在7月15日向参议院提交了一份《六月份支出概算书》。
参议员一看火更大了:你袁大总统也太拿豆包不当干粮了。现在是几月份了,7月份啊。你却拿出6月份的预算糊弄我们(敷衍了事),有没有搞错,脑子进水啦(其昏聩为何如)?
参议院立即将原件退回,限期整改。
对此,副议长汤化龙的想法很明确:"参议院万不可为政府之傀儡。"否则,"参议院、临时政府、中华民国亦将从此相随而告终矣!"
就这样三番五次,袁总统恨得牙根痒痒。他心想,别看这拨小子们现在闹得挺欢,我暂时不和你们计较,和我斗,还差得远呢,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