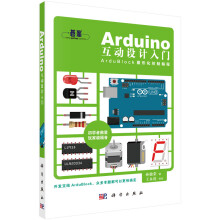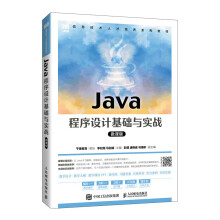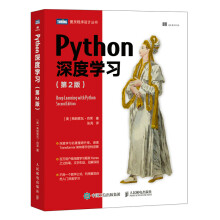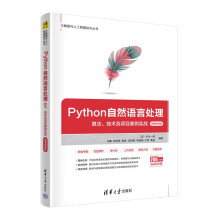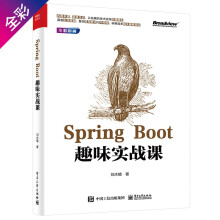我从民国三十八年四月到现在,一直从事文教工作,经常会晤的也以文教界人士为最多。其中已经逝世卓有成就者,均有人为其作传。不过这些传记的内容,多偏重于较严肃的一面,以其学术、文章、道德、事功为主。这种传记固然重要,可是我想如果能由这些人平时待人接物的细微处加以介绍,也许更可由小见大,从平凡的地方看出他们不平凡之处。我现在所要谈的,只限于已经逝世者。我的用意一方面固在发潜德之幽光;另一方面也希望年轻的一代都能见贤思齐,像他们一样,成为受大家永远尊敬的知识分子。
胡适先生
我想要谈的第一位是胡适先生。
胡适先生的传记很多,大家也都很敬仰他。胡先生生于清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西元一八九一年十二月十七日),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四日逝世。他晚年来台主持中央研究院时,由于胡先生和我是安徽同乡,常常约我在星期日到南港小聚聊天。
胡先生是安徽省绩溪县人,本名是洪骍,后改名为适。一般传记对于他之所以取名为胡适的记载,多半是说胡先生在上海求学期间,读了严复所翻译的天演论,其中有“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语,因而改名为适云云。但是胡先生亲口告诉我,他初到上海求学时,是就读于澄衷中学,后来因志趣不合,而转学至中国公学。王云五先生恰巧是他的英文老师。后因中国公学闹学潮,他遂离开中国公学。在这一段期间内,他生活上觉得非常苦闷,有一晚还被巡捕房抓去,因而对未来更感到彷徨。此时正逢北京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在招考学生,胡先生在报纸上看到这则消息后也想去应考,所以就取名胡适,意思是“无所适从”,不晓得要到哪里去之意,乃以胡适之名报考。
宣统二年(西元一九一○年)八月,胡先生考取清华庚款留美官费生,由北京到上海,坐船赴美。进入美国康乃尔大学农科,一年半后,改习政治经济,兼治文哲。民国三年六月,大学毕业随进入研究院。次年九月转至纽约哥伦比亚大学,从杜威习哲学,这也是胡先生一生的转捩点,他受到杜威博士实证哲学的影响,故一生治学特别注重证据,常谓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民国六年五月,完成博士学科考试。七月返国,八月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请,至北大任教授。十二月,与已定亲之江冬秀小姐结婚。胡先生事母至孝,在他出国这段期间,他的寡母多赖未过门的媳妇江冬秀小姐来照顾。江小姐乃是一缠脚的乡下女子,书也读得不多,以当时胡先生的声望、地位来说,不知道有多少名门闺秀视为如意郎君,但是胡先生还是遵从母命,娶了江小姐为妻。
三十六年行宪之初,由于当时局势混乱,中国国民党总裁蒋中正曾在中央委员集会中表示:第一任总统最好不要由国民党党员来担任,以示国民党天下为公的精神,最好由具有声望的社会贤达来出任总统一职。并认为胡适是最理想的总统人选。但后因一部分常务委员反对而作罢。三十七年行政院改组,蒋中正总统想请胡先生出任行政院长一职,但亦为胡先生婉拒,胡先生一生无意从政,只愿作一位执政当局的诤友。
一九五二年秋,台大校长钱思亮和我联名写信邀请胡先生回国讲学。胡先生遂至台湾大学讲授治学方法,在师范学院讲授杜威哲学,为时共两个月。在这两个月期间,我与胡先生常常见面,彼此也更为了解。胡先生善饮,时常小酌两杯,又会讲笑话,为人风趣。虽然我是他的晚辈,他总称我白如兄。
一九五三年,师范学院要成立家政系、工教系。这两个系的成立是与美国宾州大学合作的,所以我就应邀到美国考察访问一年,并经常任在宾州大学校区。我一九五三年二月由台北飞抵华盛顿时,胡先生正在华府“我国大使馆”做客,他听到我来的消息,就留了一张名片给“大使馆”的秘书,请秘书通知我有空时到纽约和他聚聚。我到宾州大学后,便写了一封信给胡先生。约定四月的复活节,前往纽约拜会胡先生。
胡先生住在纽约中央公园附近一座公寓里的五楼,我到纽约打电话给他时,胡先生仔仔细细地告诉我往他家的路线,以及公寓的标志等等。当晚,他特邀请梅贻琦先生和我共进晚餐。胡先生的公寓很小,不到三十坪,由胡太太自己下厨,胡先生则亲自端菜。由于胡太太系裹小脚,不通英语,胡先生又不会开汽车,所以买菜都是叫市场的人送到家里来的。梅先生也善饮,在席间说了许多话。可是我曾听说梅先生以前和赵畸(字太侔,山东人,北大毕业,专攻戏剧,曾任山东大学校长)两人在北京会晤时,因彼此都不善言词,见面时只各自抽支烟就分手了。因为我知道梅先生不爱说话,但是那天却看到梅先生喝了很多酒说了很多话,于是便把我过去听到这件往事提出来问梅先生是否确系如此?梅先生笑笑说:“我不记得了。”胡先生藉这次机会,介绍梅先生和我认识,最主要的用意是想让我和梅先生谈谈如何运用庚款补助师院的有关事宜。中央政府在广州撤退之前,行政院改组,发表梅先生任教育部长,梅先生没有接受,于国外出席联合国文教组织(UNESCO)会议之后,就旅居美国纽约。清华大学有一笔基金存在美国的银行,由梅先生负责保管。梅先生就拿这笔基金的利息帮助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和台湾的大学院校。梅先生知道师范学院设备不足,就答应补助五千美金给师范学院。由此可见胡先生乐于助人,他请我和梅先生吃饭,目的并不在吃饭,也希望我能认识一位教育界的前辈。胡先生曾担任普林斯顿大学东方图书馆名誉馆长一年,他嘱咐我一定要去普大参观,并打电话通知当时的馆长童世纲,要他替我安排妥当,由此可见胡先生做人做事的周到。
一九五七年六月,美国全国教师联合会在费城召开,我以贵宾身份应邀出席。路经纽约时,胡先生又要请我吃饭,我知道胡先生刚因肠胃病动过手术,应该在家休养,不宜外出吃饭,就婉谢了。在我开完会将离美返国前,他忽然打电话到旅馆对我说,他不能到旅馆话别,可是有一件事令他觉得非常高兴,他一定要告诉我。就是李田意教授对胡先生说,他前一年在日本费了很多时间,才找到《拍案惊奇》的古本,就用照相翻拍下来,这些宝贵的资料邮寄又太重,而且他也不放心,我就答应把这份资料亲自带回台湾给正中书局出版。而我自己的行李,则托师范学院毕业在美国深造的学生邮寄回国。胡先生认为我能为国外学人热心服务,深表佩慰。后来这本书在香港出版,李田意特在前言中,提及此事表达谢意。
那时候纽约有个华美协进社,社长是孟治先生,有一天举行餐会欢迎我,胡先生也出席了这次的聚会。刚巧胡先生和夫人在我前面到达,我亲眼看见胡先生在来宾的签到簿上先签胡江冬秀的名字,然后才签自己的名字。他一生提倡新思想,可是却实行旧道德,夫妇相敬如宾,白头偕老,一直为人称道。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