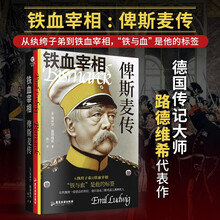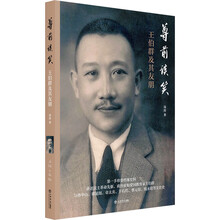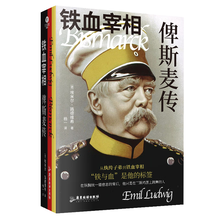16岁贤庄是别人的贤庄。无论那里有多少美好,潜藏着多少珍惜、多少牵挂,都是由一个多梦少年的遐想参与编织的虚幻,并不切实。瞿秋白无从回避的真实在常州,在景况日益困窘的家里。
1912年前后,瞿秋白一家住了近10年的星聚堂再也住不下去了,而八桂堂不属于自己,也回不去,别无选择,只得搬入与星聚堂隔河相望、觅渡桥北面的庙沿汀瞿氏宗祠。
有家归家,无家归庙,住祠堂是件极其令人不齿的事,不仅住入祠堂的一家人前抬不起头来,就是同族人也受人指责,脸上无光。无论谁家,不到走投无路,不到迫不得已,不到万般无奈,谁都不肯做这样的选择。何况,瞿家世代簪缨,官宦相继,及身通显,子孙登榜,叠荷恩荣,非到不得已,无论是哪一房、哪一支,谁肯迁住宗祠?更何况,当时宗祠里还停放着许多族人的灵柩,阴森凄凉。
现在,瞿秋白一家迁入了宗祠,仅此就可以想象他们的家到了何样的境地。
瞿家的至亲因此断绝了来往,背地里嫉恨怨诽诅咒毒害。瞿家的世交锦上添花烈火烹油。父亲瞿稚彬的心境自不待说,大家闺秀的母亲金璇更是感到情何以堪,无颜面见人。
当铺、旧货摊和米店,成了瞿秋白常去的地方。小小的瞿秋白用一包包衣物从当铺高高的柜台上换来叮当响的几纹银钱,转身去米店换回几升米或者几斤豆。为维持八口之家的生活,渐渐地,家里珍藏的金石、书画变卖一空,衣服、首饰,连柜橱、桌椅、盆桶和日用器皿,也在族人的白眼中全部典当掉了。
即便如此,有时一家的午饭只有早上吃剩的白粥。上学从街上走过,有乞丐紧追着瞿秋白不停地叫:“少爷,行行好吧!”瞿秋白收住脚步,对着年长的乞丐翻遍身上所有的口袋,说:我不是少爷。不要喊我少爷。你看,我也是一文不名啊!再不是那个双脚并拢跳过私塾高高门槛的稚儿了,再不是那个欢天喜地的少年了,困窘生活教会瞿秋白的是忍耐和承受。他变得文静起来,唯一的爱好就是独处看书,经常夜阑人静时分,仍然在昏黄的煤油灯下,手捧一卷书,皱了眉头。他的饮食甚少,经常是浅尝辄止的小半碗饭,马上就停箸不食了。在那种深深浅浅、幽明不定的寂寥中,有一种庞大而朦胧的理想在他的心田中滋长。
辛亥革命结束了帝制,中国该很有希望了。然而,换上民国的招牌,各省都督改称督军,一批昏聩腐朽、贪婪无耻的新贵摇身上台,光明只是一闪,世道渐渐变得更坏。
1912年10月10日。双十国庆节。常州各机关、学校和居民奉命张灯结彩。这是何样的国家,给予我们何样的生活,还要我们为之庆贺?!被穷困煎熬着的瞿秋白忿忿着。哪有心境张灯结彩?他特制了一个白灯笼,写上“国丧”两个大字,高挂到宗祠侧门上。轶群妹妹看到唯独自家门上悬盏白灯,觉得不吉利,也担心惹出事来,便暗暗取下。瞿秋白知道了,“追打”妹妹:你别跑,为什么要把我挂的灯笼摘下?妹妹逃远,瞿秋白转身把白灯笼重新挂起。
极度苦闷中,瞿秋白去了中学堂侧的红梅阁。红梅杳然不见,只剩下落红无数,斑斑点点。临阁望天,瞿秋白想到的是唐大中二年一书生登滕王阁挥就的一记中的句子:“或散霞成绮而宜晴,或山色空蒙而宜雨,或千岩竞秀而宜春,或江青木落而宜秋,或一碧万顷而宜月,或孤舟独钓而宜雪,或西山爽气而宜朝,或翠屏晚对而宜暮。”这“或”那“或”都是文人的假设,从浪漫的想象回到现实时,那份艰困,瘦肩难当。
极度苦闷中,瞿秋白治印消遣。他替羊牧之刻了一篆文名章。章上的“羊”字两角刻得特别大。羊牧之接过,不满“羊”角太大,要瞿秋白重刻。瞿秋白笑着说羊牧之不懂,羊角是用来防卫和战斗的,不大行吗?角大才能克敌,角大才能摧坚。
1915年初,大姨妈阿叙嫁到无锡驳岸秦家的女儿杨庆令(小名壬壬)来常州瞿家做人工流产,想请人织双袜子御寒,费用一元,瞿家已支付不起。
瞿秋白的四弟阿森(后改名景白)鼻子上生疮,疼得他直哭。可是,家里没钱给他医治,只能任其溃烂,最终阿森成了塌鼻子。
阿森命还算硬,只是塌了鼻子,而二妹红红,三岁那年突发高烧,母亲把毛巾扔到冰冷的井水里绞一把,迅速敷到她的额头上,能用的土法子都用了,就是退不下去烧。郎中说是肺炎,可家中空徒四壁,无钱抓药,就见高烧中的妹妹哭声越来越弱、越来越弱,游丝一般,最后没有了气息……弟妹们的学费当然付不起,一个接一个地停了学。妹妹轶群不得不时常住到舅舅家中。大弟云白则过继给了擅金石的六伯父,随嗣母费氏住。塌了鼻子的二弟景自在宗祠后翻轩内由母亲授以《论语》、《唐诗》。
面对拮据,瞿秋白与母亲经常有相对无言却彼此心灵渗透的对望。
1915年夏天,正是常州城中黄莺婉转啼唱于橘树之上的明媚季节。就在这个季节里,因家中再也拿不出一文钱缴纳学费,母亲只得让离高中毕业还差半年的长子瞿秋白辍了学。
尽管瞿秋白并不为没能读完中学而感到怎样的痛苦,他最能理解为这个破败之家操碎了心的母亲,但这对母亲则是一个极大的刺激,她无尽地叹息:阿双当有好前程的,是可以光大门楣的,只可惜眼前的家境,大概是要耽误了。
1915年中秋节到了,言辞峻刻的讨债人堵门逼索,迟迟不走。粘贴在瞿家房门后面的债单有寸厚。这些债多半是瞿秋白的奶奶生病时欠下的。要等到我70岁,才能还清这些债了!——厚厚的债单令金衡玉无限悲伤。她卑微地向讨债人再三道歉求情:再延几天、再延几天吧。有了,我一定还。
1916年1月(农历乙卯腊月)下旬,在邻居们欢乐地准备年货、自己家中灶冷甑尘的年关,金衡玉提笔给无锡的杨庆令夫妇写信,邀他们来常州。接到舅母(杨庆令习惯于这样称呼金衡玉)的来信,杨庆令偕丈夫秦耐铭来了。
金衡玉尽其所能,备些薄酒素菜款待耐铭夫妇。席间,她请求耐铭夫妇把阿双带到无锡去:阿双年龄大起来了,他的父亲不管一切,最好跟你们在一起,可以长些学问。
秦耐铭与杨庆令1911年农历八月二十一成婚。按照民间习俗,婚礼后的次日,女方亲戚需要到男方这边来会亲。杨庆令自幼寄养在瞿家,瞿家自然就是她的娘家。农历八月二十二,瞿秋白随父亲瞿稚彬来到无锡秦家。12岁、个子尚小的瞿秋白,言语行动文雅规矩,表姐夫的亲戚夸赞他好像成年人。面对舅母的恳求,秦耐铭一口应诺。
细心的母亲担心儿子放心不下自己,转而嘱咐道:如果能在无锡久住,觅到一个职位,每月可得些钱,家用也就渐渐有希望了。常州离无锡仅百里,来去便当,尽可回家来看我。
母亲的话虽凄楚,但平静而亲切,瞿秋白没有觉察到任何异样,心中翻滚的是清代常州诗人黄仲则“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的句子。
次日,按母亲的嘱咐,瞿秋白找剃头佬理了个发,穿上母亲刚刚亲手缝制的蓝衫——瞿秋白是看着母亲一针一线缝起的,当冰凉的针穿过棉布,仿佛千疮百孔的岁月,仿佛密密麻麻的体贴——与秦耐铭夫妇一起,去了无锡。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