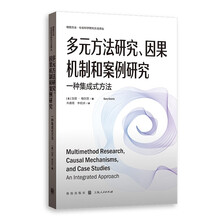第三,我们必须在心中牢记,在人权和公民权的范畴内,政治性地正确认识历史责任已经在国际舞台上成为鲜明标准。这些标准也越来越成为世界各地所经常遵循的共识。这种发展始于20世纪70年代,当时出现了各种解放运动和争取公民权及人权的运动。随着冷战结束,两大超级国家的阵营体系终结,这种发展得到了新的动力,并已经成为全球化世界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到目前为止,任何民主国家、希望维护其声誉的跨国公司或全球范围内活动的非政府组织,都会把自身同那些在政治上无法正确处理或合适对待“困境性”过去的盟友之合作视为政治自杀,他们会公布关于国家施行暴力的知识①、竭力赔偿受害者,以及(最后)适当地修正其国家的宏大叙事和历史教科书。这一进程的自然结果便是,许多国家的民族主义煽动者联手反对为世界所接受的标准,并煽动现存的历史教科书争议去面对所谓的“受虐性的历史观”(这是日本人的宣传标语)。
第四,我们希望进一步指出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全球化、以及地缘政治上重组空间和信仰的时代对民族国家和传统的国家身份构成了一种极大的挑战。民族国家比以往更努力地追求国家融合,它们持续地为绝大多数民众提供日常生活和政治谈论的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指导。民众只能在民族国家中寻求保护。唯有民族国家才能让民众获得社会福利、经济成功、国际竞争力,并参与到一种荣耀的集体身份中。
据此,任何有可能削弱民族国家的举动都会轻易地引发民众的不满。这同样也会轻易地让大众媒体去宣扬这种担忧:例如跨国企业的超级经济权力、日益增长的全球就业竞争、全球性移民浪潮的兴起、超国家机构和组织对国家政治的影响力上升,以及(最后,就欧洲而言)民族国家消融到一个超民族的国家中(即欧盟,1992年)。
在面对民族国家、历史教育和国家认同的相互关联中,一方面,政治家和立法者不断倾向于用法规来规制历史讨论,以便解决国内政治争议;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对于公共历史教科书争议的不断开放态度,即便在那些至今为止仍然完全不熟悉这种争议的国家中——因为它们的国家认同和集体记忆建立在一个广泛的一致意见之上,如荷兰——也是如此。①关于新教科书的争论,以及这些新教科书是否可以把荷兰历史有效地灌输到年轻人的集体记忆中的争论,被十分轻易地等同于(真实的或被媒体虚夸的)对其国家身份的担忧——在保守的宣传家们看来,这种国家身份受到了移民、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三方面威胁。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