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缪出身贫寒,却引起一个小学教师的注意。这位小学教师引导他去读书,建议他申请地方中学的奖学金,并且一直守护着他一步步走向成功。在阿尔及尔贝尔库城区的贫民区,加缪与他的哥哥吕西安以及单身汉舅舅艾蒂安住在一起。在这个由女人统治的家庭里,暴虐专横的外婆主宰了家中的一切,温顺善良、目不识丁的母亲丧失了部分听力,几乎沉默无语。加缪的父亲是一个酒窖工人,为当地几家葡萄园酿造葡萄酒,曾在“祖阿夫”兵团服役,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奔赴法国战场,在马恩河战役中不幸阵亡,当时加缪还是个婴儿。“祖阿夫”兵团主要从居住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移民中招募士兵,士兵身着红蓝搭配的彩色阿拉伯制服,这使他们看起来像一面面战旗。该兵团是突击部队,在战斗中伤亡惨重。从加缪父亲头部取出的炮弹碎片被法国政府送返回乡,置于一个旧的饼干罐里放在厨房,而他父亲获得的法国十字勋章则被封在镀金的相框里,放在餐厅。当时加缪全家住在一套三居室的小套房里,阿尔贝和吕西安挤在同一张床上,与母亲合住一个房间。房子里没有浴室,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厕所就在门厅;厨房里没有烤炉,所以每隔几天,阿尔贝或者他的哥哥就得托着一大盘食物到附近的一家肉店去将它们弄熟。这些细节在《第一个人》(加缪去世前正致力于创作的作品,是一部带有明显自传性质的遗稿)中得到真实的再现,没有经过任何特殊的戏剧渲染和篡改,因为在贝尔库,这些都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了。他们住的房子有一个凸出去的小阳台,从阳台上可以看到下面繁华的里昂大街,那是另一个世界:林立的商店、咖啡馆,人潮拥挤的市场。大街上人声鼎沸,人们操着五花八门的语言——法语、阿拉伯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还不时传来手鼓和响板的伴奏声,“咻咻”的驴嘶声,有轨电车经过时“叮当叮当”的铃声。各种混杂的气味也阵阵飘过来:藏红花、大蒜、茴香、鱼、腐烂的水果、金银花、茉莉花等等。太阳热辣辣地照在头顶上。海水在房屋的边缘漾着波纹。
路易斯·热尔曼是加缪的小学老师,也是第一个像父亲一样关注他的人,在热尔曼的精心呵护下,加缪成为一个模范生,严肃认真,稳重缄默,同时又机灵好奇——一个智慧的典范,热尔曼总是这样评价他。加缪喜欢学校的功课,也喜欢学校的生活,所以进步很快,不久就成为班里最优秀的学生。加缪的优异成绩帮助热尔曼说服了他的母亲,同意让他进入中学继续学习,而不是像他舅舅那样到当地的箍桶匠那里去干些制桶之类的活计。在上学之余,加缪过着与那个街区其他任何男孩一样的生活,只不过生活在他身上体现的方式以及他体会生活中每一个细节的方式有所不同罢了。加缪喜欢读书,还喜欢体育运动。他与一群伙伴一起,在大街上用杏核、石头或木棍做游戏;到公园里爬树;分享刚刚做成的卡拉梅尔奶糖,被他们称作“tramousses”的干羽扇豆籽,或者在某些特殊时候才能吃到的一袋炸薯片;他们去海滨游泳(兼洗澡),大声喧闹着,在水中上下翻跃,纵情支配着他们的生活和那片海域,“就像贵族们一样,确信他们的财富是无穷无尽的。”即使无聊也成为“一场游戏,一份快乐,一种刺激,”他在《第一个人》中写道。
加缪用平和的语气和温暖的心情回忆着他童年生活中那些最单调乏味的事情:每晚都要熨烫的唯一一条裤子;那些钉在鞋底的钉子,不仅可以查验他是否违禁去踢球了,还可以避免把鞋底磨坏;每天午后迫不得已陪外婆一起睡的午觉,以及忍受她上了年纪的身体散发出来的体味。(长大成人后,他承认自己恨透了那样的午睡,以至于从那以后,除非病得卧床不起,他绝不允许自己在午后躺下去睡觉。)在后来的岁月中,当加缪对巴黎的所有幻想都落了空,感觉自己像一个被困在钢筋水泥构筑的城市森林中的外星人的时候,正是这些回忆支撑着他。在他大多数的抒情散文中都可以找到这种乡愁。加缪说,每一次返回阿尔及利亚,他都感到令人喜悦的安慰和释然,“在大海的宽脊上,他得以喘息,在波涛中喘息,在明媚阳光的摇曳下,他终于可以睡觉了,终于回到他始终留恋的童年,回到那曾帮助他生存、帮助他克服一切的阳光及温暖的贫穷中,回到这样一个秘密中。”
加缪就读的那所中学坐落在国际大都市阿尔及尔熙熙攘攘的市中心,因此吸引了大批来自于这座城市富人区的多种族的学生。正是在这所学校里,加缪第一次对自己的出身萌生了自我意识,感到自己并非是一个无意识存在的普遍个体,而是“与众不同”的。他说,在那之前,他一直以为所有的人都像他一样。而在那所中学,他学会了作比较。他是个荣获奖学金的优秀生,被誉为“民族的学生”,不过这个称谓不仅阵亡士兵的儿子们可以获得,军队和政府官员以及法国殖民地官员的儿子们同样可以获得,但他们的衣着更加体面,他们的房子高高地位于小山之上,更加富丽堂皇。在进入这所中学的申请书上,加缪不得不把自己的母亲描述为一个家庭妇女,或者说清洁女佣;这突然让他充满耻辱感,然后“为有这种耻辱感而感到羞耻”。但对母亲地位的质疑,比如说外婆凌驾于一切之上的权威,或者他自己逐渐意识到的母亲的愚昧和无助,却在他内心深处激发起对母亲温和的忍耐力更加深刻的尊敬,以及愈发强烈的、想要予以补偿的爱。加缪的母亲曾经尝试过一次短暂的恋爱,那使她重新变得兴高采烈、神采奕奕,但被她的母亲和兄弟艾蒂安粗暴地压制了。每每回忆起这些来,加缪都感到愤怒和悲哀。在他整个一生中,他都为保护和尊重这个沉默的人而备受煎熬,因为母亲的无知和耳聋将其与外界隔绝开来:她不能读报,也不能听收音机,她不知道历史和地理究竟是什么,她没有任何期望或者明确的渴望,她“不敢渴望”。
加缪本人的生活可以说是对他母亲生活的一种反叛——对于她的顺从,他报之以野心;而她的逆来顺受则唤起了他不知疲倦的激进行动。在生活的方方面面,几乎都出现了这样的反差。加缪清楚这一点。《第一个人》是他打算创作的以爱为主题的系列作品中的第一部,他把它奉献给了寡妇加缪,“献给永远不能读此书的你”。在写给自己的一则笔记中,他说道:“两个人的历史,他们的血脉相通,却迥然不同。她恰似这世上完美的化身,而他是沉静的怪物。他投入了我们这个时代所有的疯狂中;她穿越了这同一历史,却如同走过其他平常的时代。她大部分时间缄默不语,只会用几个词进行表达;而他滔滔不绝,千言万语却无法寻到她仅以静默所表达的东西。母亲与儿子。”
……
展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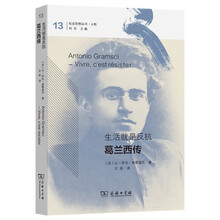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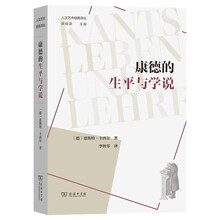
——斯文·伯基特(SvenBirkerts),《波士顿环球报》
形象地洞悉了自加缪少年时代起便开始发作的肺结核病是如何使他陷于疲惫的同时又激发了他,豪斯确切地注意到这种疾病如何增大了他的放逐感以及作为局外人的感觉……关于萨特在公共场合对加缪性格和作品的攻击,豪斯提供了详细的细节,这是一次昔日友人使人痛苦的背叛。
——《科克斯书评》
一丝不苟的传记作品,回忆录……来自那个时代、那些场所和人物的细致而生动的图片塑造了加缪的生活……一部迷人的、充满生气的,极度热情且独特的传记作品。
——《图书馆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