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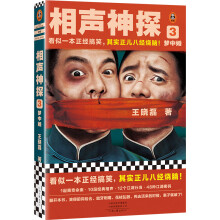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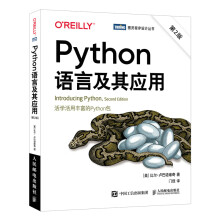






《运动通史:从古希腊罗马到21世纪》第一次完整呈现人类运动5000年的斑斓历史。正史的严谨,图史的绚烂,逸史的风趣。诸多生动细节,200多幅精彩图片,5000年丰富知识。
海报:
古埃及体育:奔跑的法老
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王朝的埃及国王都喜爱运动。当然只有那些法老——世界秩序的担保人——可以胜出的运动项目才会得到艺术表现。他不可能是一名竞赛者,因为他当然总是赢家。法老登基时跑步成为礼拜仪式中的核心内容,它大概象征着对领土的拥有权,同时也是法老力量的展示。自从外族统治者希克索斯(Hyksos)在公元前17世纪从东部侵入尼罗河谷并统治下埃及后,对法老的艺术表现发生了变化。起初埃及人无力抵抗骑着战马、驾着战车并使用复合弓的外族人。外国统治者被驱逐后(第18王朝),法老们纷纷让艺术家表现自己在马拉的战车上抗击敌人的场面,这需要相应的体能(驯马、驾车、射箭等)作为先决条件。也许并非巧合的是,古埃及历史上没有别的时期像这个王朝这样有过这么多表现体育场面的作品,因为反抗异族唤醒了他们的尚武精神。从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III)开始,埃及人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每年都向邻国开战。使用武器像体育运动一样需要不断地训练,射箭到底是体育还是军事训练也就很难分清了。
与国王的情况不同,在社会的其他阶层竞赛是可能的,而且也经常被表现。在第五王朝的一个墓碑上(普塔霍特普[Ptahhotep]大臣石室墓,萨卡拉)就可见到青少年摔跤的场面,有的正在交手,有的在用过桥动作摔。纸莎草纸和浮雕上的摔跤场面一直到希腊统治时期都时常出现。位于贝尼哈桑(Beni Hassan)的古埃及州长 巴克提三世(Bakti III)墓中的摔跤场景最著名,它们就像一本摔跤教科书,展示的姿势不少于219种。摔跤手们除了一条专用的类似日本相扑的兜裆布外,别无所覆。
坟墓中表现体育比赛场面的作品可能意味着法老生前喜欢这类体育活动,但这类活动也可能是——像后来在希腊和罗马那样——作为一种荣耀专门在葬礼上为他举行的。因此,击棍似乎在死去的图特摩斯三世墓旁进行过。相应的图像在第十九王朝初才完成,然而它们仍就是迄今表现葬礼活动的最古老的作品。阿蒙霍特普二世(Amenhotep II)让人在卡纳克(Karnak)阿蒙神庙(Amuntempel)玫瑰色花岗岩石柱上将自己刻成弓箭手,正在从一辆战车上向敌手射箭。1936年此石柱被发现,其局部画面被出版,这才使体育主题成为埃及学中必不可少的研究内容。在古埃及文物中,我们见到详细表现赛跑[16]、跳远、战车赛、射箭、拳击和摔跤[17]、击棍、爬杆、舞蹈和杂技场面的作品。球类游戏画面则是罕见的,但一些球被保留下来。水上运动场面则有游泳、潜水、叉鱼和划船以及一种水上比武,在德国它被叫做“渔夫打擂”:两艘船对开,双方船上的人分别用长竿子试图把对方船上的人打下水去。[18]与其他贵族社会一样,狩猎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掷矛和射箭,投镖(打鸟)和扔索套(捕公牛)技术至关重要。
这些运动项目中的大多数后来在整个地中海区域广为传播,因此人们要问,后来的文明——如克里特岛的米诺斯或希腊文明——在多大程度上受到过埃及文明的影响。[19]虽然许多从古埃及流传下来的证据——大多数铭文和艺术作品是颂扬诸神或法老的,或是与死亡祭仪有关——来自礼仪范围[20],但希腊人仍然视其为体育比赛。在最早的希腊文本中,如荷马,就有关于法老的射箭艺术的记载。哈利卡那索斯(Halicarnassus)的“史学之父”希罗多德,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亲自去过埃及,曾报道过那里的各类比赛和体育仪式。此前一个世纪,甚至有一个由奥竞会组织者组成的代表团被派往智慧的埃及人那里,“以便听取他们对奥竞会竞赛规则的评价”。
古希腊运动:嘴的仆人?还是城邦英雄?
罗马的建筑理论家维特鲁威(Vitruv) 嘲笑运动与运动员的百无一用时说,一位运动员在奥林匹亚的某次竞赛中能够保持不败纪录,这对人类究竟有何益处?
维特鲁威是在秉承一种悠久的运动批评传统。从哲学家柏拉图开始,就曾怀疑专注于肌肉的功用可能会阻碍才智的养成。希腊剧作家欧里庇得斯在其剧作《奥托吕科斯》(Autolykos)中讥讽运动员,说他们因需要大量卡路里而成了“嘴的仆人”和“胃的奴隶”。他认为,希腊公民更该注意让自己的城邦有好的统治,而不是不断成群结队地涌向奥林匹亚,在那里向那些吃货们欢呼喝彩。出于纯粹的平民主义,政治家们不去促进人类的真正美德,而是允许这类胡闹继续下去。
与古典时代晚期不同,当时的人并非出于宗教原因批评运动文化,因为这些竞技比赛是在敬神节(Panegyris)期间在宗教敬拜场地为了对诸神表示敬意而举办的。奥林匹亚大概最初就是一个地方性的祭礼场所。自公元前11世纪始,人们就用动物作牺牲来供奉神明,多用牛和马,也有用羊和狗的。在古典文献中也总是提到这一带土地十分肥沃,在古希腊——与许多其他文化一样——土地肥沃被视为诸神的馈赠。顺理成章,这里尊崇的是主掌丰收与生育的女神:阿尔忒弥斯(Artemis)或阿佛洛狄忒(Aphrodite),得墨忒耳(Demeter)或大地之神盖娅(Gaia)。最晚从公元前7世纪开始,奥林匹亚就成了宙斯(Zeus)的圣地。除了宙斯神庙外,这里也敬奉其他神明,但这些神明的庙堂都是后来才建成的,比如赫拉(Hera)或神的儿子大力士赫拉克勒斯(Herakles)的庙堂。
慕尼黑的古代史学者克里斯蒂安·迈尔(Christian Meier)在阐释奥林匹亚竞技游戏的意义时,是从关注希腊文化的几个特点着眼的。希腊文化的突出特点就是城邦,这些城邦非常在乎其政治独立性。即使在公元前8世纪希腊殖民时代,当环地中海和黑海建立起许多新城市时,希腊人也未建立大帝国,而是通过政治上和军事上的联盟来抗击城邦的内外敌人。独立的城邦需要沟通场所,以保持其文化共性。诸神的圣殿便为他们提供了这种场所。偏远的奥林匹亚的优势在于,它的崛起让希腊各城邦都无法占地利,其圣地地位在全希腊受到承认。[4]引人入胜的体育比赛提升了圣地的声望,反之亦然。无论是在古老的贵族文化中,还是在民主时期,公众和竞技比赛在大希腊(Magna Graecia)都起着重要作用。各城邦的竞争与其说是通过战争,还不如说是通过体育竞赛来进行的。文化史学者雅各布·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认为竞赛体现了希腊文化的本质特征,从而塑造了竞争这一概念,他认为这是希腊文化的原动力:抗争、公开竞赛、成就、志向。
希波战争时,在最后时刻,雅典、斯巴达和科林斯结盟,使战争发生了转机,首先在萨拉米斯(Salamis)海战中取胜,然后于公元前479年在普拉提亚(Plat?a)再胜。得胜将军提米斯托克利(Themistokles)于公元前476年参观了奥林匹亚,在那里他被人们当作英雄来拥戴,很多运动员因被他抢去了风头很恼火。由于只有通过联合行动才成功地抵抗了来自波斯的危险,人们想出一个主意,在奥林匹亚的宙斯圣殿设立一个仲裁法庭,来和平解决希腊内部的纠纷。考古挖掘出的文献中就找到公元前476和472年的两个冲裁判决。
奥林匹亚成为所有希腊人和睦相处的象征。在此背景下奥竞赛首次出现术语“神之和平”(Ekecheiria [握手言和])。公元前476年在历史上是奥林匹亚圣殿的关键年。这一年的意义在于人们开始兴建全新的宏伟的宙斯神庙,在后来的几百年中它会成为奥林匹亚的圣地。
古希腊时间:奥林匹亚运动会纪元
随着希腊向地中海区域殖民和抵御外敌越来越需要政治上的协调,一个共同的参照系就显得不可或缺了。历史学家修昔底德用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开始来协调不同的希腊纪元。生活在西西里陶尔米纳(Tauromenion)和雅典的希腊历史学家提马埃乌斯(Timaios)将公元前300年的绝对零点时刻与一份奥竞会获胜者名单联系在一起,从而开创了以奥竞会纪元的先河。不久,数学家和史学家昔兰尼(Kyrene)的埃拉托斯特尼(Eratosthenes)就用臆想的奥竞会之起始时间来纪元。自从公元前776年奥竞会定期举行后,人们就找到了一个获得公认的参照框架。历史学家桑索理努斯(Censorinus)和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甚至用第一次奥竞会的举办来标识绝对纪元。这样奥竞会就成为整个希腊史学的基础,其重要性远远超出原来的祭祀节日或泛希腊体育赛事,如所谓的公元前276年的《奥竞会年鉴》(Olympische Chronik)所记载的。[8]奥竞会的开始作为时间长河中的中流砥柱,在希腊纪元中所发挥的作用相当于基督教纪元中基督的诞生。甚至罗马人在协调希腊和罗马帝国纪元时,也使用古典的奥竞会纪元。此奥竞会纪元方法流行了数百年,直到古典时代晚期它都影响着人们的时间概念。
体育一开始就和商业暧昧:人民的体育,人民的生意
泛希腊、区域和地方比赛数目之多,以及体育设施的数量和质量都表明,在古希腊体育不是小众的事情,而是必须汇集大量训练有素的年轻男子。这支队伍绝不局限于一定的社会阶层,如青年贵族或下层市民。哲学家柏拉图就建议所有的年轻人——当然他指的是男子——参加五项全能比赛,这意味着必须定期参加跑、跳、投掷和摔跤训练。竞技教师还必须掌握心理学和雄辩术。系统培训(Gymnastikos)当然需要专职教练(paidotribai)。诗人品达列举了五种竞技体育专家。在古希腊晚期流行一种被叫做“四体系”(Tetradensystem)的训练方法,四天为一个单元,训练强度各有不同,同时运动员还要吃规定的运动饮食(anankophagia)。希腊的体育场显然对公众开放,在罗马,群众性体育运动则是在巨大的露天公共温泉浴场和帝国时期的私人浴场进行的。这些地方开展的首先是球类游戏,当时还没有各类专用的球类运动场。[30]
公众对体育赛事极感兴趣。公元前5世纪观众座位就已经是阶梯式逐渐升高的了,以便所有的人都能看到运动员。而在下一个世纪,至少体育场的看台都是由石材搭成的。至于观众对体育所表现出的热情我们知道许多例子,一个有代表性的是来自利姆诺斯(Limnos)岛的诡辩家菲洛斯特拉托斯(Philostratos)的描述:“他们尖叫,从自己的座位上蹦了起来,这里有人高举双手,那里有人从地上一跃而起,还有人高兴得和邻座抱在一起,因为真正令人兴奋的比赛,观众是不会保持镇静的。”[31]这位作者本人就得到过殊荣,雅典市为他在奥林匹亚塑了全身像。[32]菲洛斯特拉托斯著有“论希腊人竞技”的论文,重点描述奥林匹亚竞技会,但与其上述形象化描述不同,该论文很长时间仅以片断的形式流传下来,直到19世纪全文才被重新发现。这篇论文的写作时间得以确定,因为文中提到成绩斐然的运动员喜力克斯(T. Aurelios Helix),他曾是213和217年的奥运冠军,219年他又摘取了罗马卡比托利欧(Kapitolien)运动会的双料冠军。[33]
体育热的持续不仅导致体育设施的兴建,也出现了“体育用品制造业”,此行业制造比赛和训练必需的器械。如果说跑步时——因为运动员是裸跑——还不需要什么装饰品,五项全能中跳远的情况可就不一样了。带把手的助跳器(halteres)是专门为跳远制作的。考古发掘出的文物表明,这种助跳器有铅质或粘土的,其重量在1.5和4.5公斤之间。同样,铁饼也是纯粹的体育器材。它们——在形状相似的情况下——重1.4至4.8公斤。估计在同一场比赛中,运动员使用的铁饼是一样重的。标枪比赛中使用的标枪比战争中使用的长矛要轻得多,它们大约有指头那么粗,长度相当于身长,其顶端被磨钝,以免发生意外。
罗马的野蛮:角斗士游戏
在社会学意义上,如果试图从一种游戏或某种特定的运动项目来解释一个社会的核心价值观——如希腊的奥竞会、巴厘岛的斗鸡或是美国的棒球比赛(见引言)——那罗马帝国的角斗士游戏(Gladiatorenspiele)[此词来源:gladius=剑;gladiator(角斗士)=剑客]则是不二选择。在罗马帝国的核心部分和外省,大斗兽场(Kolosseum)及其他圆形竞技场与圆形剧场(Amphitheater)首先是为这种游戏建造的。许多罗马作家质疑希腊竞技赛或是罗马戏剧,但即使在共和时期,更不用说在帝国时期——除了哲学家塞内卡[45]外——没有著名作家拒绝过角斗士游戏。甚至连古罗马晚期的基督教作家也不例外。虽然他们担心角斗士的灵魂能否得救,但却不敢撼动角斗士游戏,因为它是罗马众口一词受到称赞的伟大游戏。但是,这种游戏到底为什么这么吸引人呢?它究竟是什么样的游戏呢?
角斗士游戏(munera [穆内拉],拉丁文munus的复数形式,=礼物)大概起源于罗马之前的伊特鲁里亚。为了荣耀死者,伊特鲁里亚人的殡葬仪式包括“死亡游戏”。输家必须付出生命作代价,穆内拉在一定程度上是献给神明的祭品。后来这种游戏变成了送给参加纪念活动者的礼物,再后来更成为给公众的礼物了,输家也并非一定要死了。它们纯属私人创意,从来都不是官方祭礼的组成部分。公元前264年,罗马的一次葬礼上有三对角斗士互相厮杀,这是最早的角斗记载。这种习惯受到青睐并首先由贵族采纳,各家族之间争相举办场面最壮观的角斗士游戏。公元前216年举行的李必达(M. Aemilius Lepidus)的葬礼上,在广场上搏斗的角斗士已经达到22对。根据维特鲁威的见证,约公元前200年在罗马广场改造时就已经考虑到举办角斗士游戏的需要了。[46]凯撒(Gaius Iulius Caesar)于公元前46年为庆祝其胜利所举办的角斗士游戏,无论从质量上还是其辉煌程度上都是登峰造极的。这场庆典是以其妹妹的葬礼为借口举办的。罗马角斗士游戏的举办者其实对其祭礼缘由并不感兴趣,相反,他们让此游戏与葬礼脱离了关系,而是用它来增加自己的知名度,如果他们竞选某个重要职位(市政官、财务官、行政长官)的话。
在共和时期角斗士游戏的重要性已有增加,这在以下措施上可见一斑:自公元前105年起,为了提升部队的斗志和效率,角斗士被接纳为罗马军团的教官。公元前42年开始,一些地方行政官开始允许在官方举办的活动中插入角斗士游戏。公元前22年,首位罗马皇帝奥古斯都重新颁布了全国所有大型活动的实施办法。他规定,角斗赛每年由行政长官组织举办,参加的角斗士数量不得超过120对,以结束举办者间的割喉式竞争。至此,角斗士游戏与葬礼的关系正式终止,它成为罗马人的民族体育,这种国家娱乐项目为罗马的节日日历提供了框架。克劳狄(Claudius)皇帝最终将举办年度角斗士游戏的工作委托给财务官委员会。公元80年,图拉真皇帝为庆祝战胜达契亚(Daker)人举行的角斗士游戏无疑是成本最高的,123天内投入了1万名角斗士。[47]
帝国时期说起“面包和娱乐”,娱乐首先指的就是角斗士游戏。为什么这种游戏对罗马人有如此大的吸引力呢?角斗士实际上是由一些这样一些人充当的:即奴隶、战俘和重罪囚犯。当然也有志愿者,他们宣誓在合约规定的时间内接受一种类似奴隶的身份。他们这样做有时是有难言之隐,但更多情况下是出于冒险欲望,想一举成名。志愿者和其他角斗士一样要在训练营接受培训,其中规模最大的是罗马的ludus magnus(大角斗培训学校),它可同时容纳2000名角斗士。此外,帕加马(Pergamon)、亚历山大和卡普阿(Capua)亦有大型角斗士学校,但仅罗马一地就拥有其他几个培训中心。角斗士们不是业余爱好者,而是训练有素的职业斗士。这些体魄健壮的运动员魅力无比,有妇女为了角斗士宁愿抛弃原有的家庭。这项运动本身也非常有吸引力,以致一些罗马上流社会成员愿意以角斗士身份出场。年纪较老的皇帝提比略(Tiberius)把所有自愿充当过角斗士的骑士阶层和元老院成员从罗马驱逐出去,然而,年轻的皇帝康茂德(Commodus)作为一国之君甚至亲自上了擂台,因为他想“让竞技场赢家的光彩再沾些帝王气”。[48]无论是用捕网(retiarii )和三叉戟的运动员,还是用短剑和圆盾(mymillones )的运动员,进行这种搏斗其实都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他们可能终生致残,在自愿弃权情况下——每个角斗士都可以举手中断搏斗——由角斗场的观众决定角斗士的生死。他们并非总是投票让角斗士去死,这一点从一位角斗士的墓碑上可以看出,这位名叫弗拉摩(Flamma)的角斗士曾四次获释,但他一直没有放弃做角斗士。在他位于西西里的墓碑上写着:“弗拉摩,轻装角斗士,活了30年,参加过34次角斗,赢了21次,平了9次,输了4次,他是叙利亚人。德里卡图斯( Delicatus)让人立此碑纪念他这当之无愧的战友。”[49]
对奴隶、罪犯和战俘而言,被光荣释放的激励——如果他们存活3年以上,就保证能获得自由——通常却只是个模糊的前景。因为作为角斗士每年必须大约赢得两到三次博斗,这意味着在赛场一共要胜出六至九次。此后还得在训练营再服务两年,但不用再去角斗场。作为获释者他们是享有最低权利的公民,不能担任公职或服兵役。这种限制的原因之一是:成功的角斗士——犹如今天的体育明星——人气太盛,又拥有财富,会成为一种政治因素。作为英雄他们体现着罗马民族的美德。能够获胜的角斗士拥有勇气和勇敢、纪律和战术、推断力以及视死如归的精神,这正是罗马秩序优于其敌人的地方。游戏的组织者和观众在获胜者身上寻找认同,用他们的英雄行为验证自己的想象。游戏自然是为了提供娱乐,但同时观众在共同经历的惊心动魄以及随后的评判仪式中又可以体验一种归属感,即对罗马、皇帝或各省精英的认同。也正是因此,角斗士搏斗——连带其相关建筑竞技场——能够在整个罗马帝国传播。它与罗马帝国是并荣并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