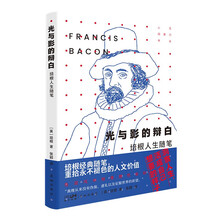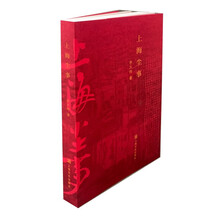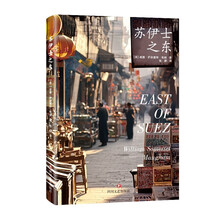摇曳秋风遗念长 孙晓玲 一落黄泉两渺茫,魂魄当念旧家乡。
三沽烟水笼残梦,廿年嚣尘压素妆。
秀质曾同兰菊茂,慧心常映星月光。
老屋榆柳今尚在,摇曳秋风遗念长。
父亲这首旧体诗《题亡人遗照》(即《悼内子》),写于1970年 10月26日下午,距我母亲去世仅半年时间,充满赞美的怀念,寄托了父亲飞鸿失伴后的不尽哀思。
母亲叫王小丽,这个名字还是进城后为上街道“ 识字班”父亲给她起的。她是与父亲同县的一个普通而又有着传统美德的农村妇女,二十一岁时嫁给了正在保定读书的父亲,六十一岁时悲惨地逝于血雨腥风的“文革”之中。印象中的母亲,稍圆的脸盘儿、双眼皮大眼睛,宽脑门儿白净皮肤中等个头儿,待人亲切乡音极浓。她总是穿得素素净净的,是家做的那种偏襟布衣,鞋也总是自己纳底儿做。虽然没有上过学,可她记忆力不错,语言特别丰富,民谣乡谚经她说出来,一串儿一串儿地既押韵上口又风趣生动,我到现在还能背出十来段儿,像什么“有爹有娘仙桃果,没爹没娘风落梨”、“有享不了的福,没受不了的罪 ”、“腰里揣着一文钱你想花十文棍,给你个老母猪也不够你胡打混 ”等等。可以说我的启蒙教育,很大一部分都是从这些带有“警世性”的“土语村言”中获得的。
我们几个孩子还在上学的时候,父亲就极其严肃地教育过我们:“从小我对你们没尽过什么责任,你娘把你们拉扯大可不容易,你们都要记着!” 父亲语重心长的话字字千钧。我们都知道,自从大哥普不幸夭亡后,四个孩子无论哪个头疼脑热,母亲都紧紧地抱在怀里,在农屋土炕上伴着用棉花捻儿自制的小油灯,走来走去地彻夜不眠,直到捂出汗、退了烧,才会放下紧绷的心。母亲就是靠着这种执著、这种坚忍、这种无私的爱,在战乱离别中,在缺医少药的穷乡僻壤,抚育大了我们,令我们终生感恩,春晖难忘。
在父亲的《荷花淀》、《嘱咐》、《丈夫》中,我都看到了极其熟悉的举止身影。其中有些对话,仿佛“原封不动”就是母亲讲的。
我甚至这样想:如果没有我母亲这么善良质朴、柔婉多情和心灵美的妻子,也许就不会有《荷花淀》;如果没有我母亲对父亲无私的爱和倾力支持,父亲就不可能在延安的土窑洞里,使着劣质的笔,蘸着自制的墨水,在粗糙的草纸上,饱含激情、行云流水般地写出那些优美文字,就不可能连草稿也不打,自然而然“就那么写出来”诗样文章。父亲的文字中,固然有对人民战争的颂扬,固然有自身情操的内涵,固然有对冀中英雄妇女五体投地的敬佩,可一定也有对遥遥相盼千里之外妻子的思念,有对妻子绵绵的爱。
1942年中秋夜晚,父亲在山地阜平一挥而就写下了短篇小说《丈夫》,载于12月份的《晋察冀日报》。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曾亲口对韩映山说过,此文是以妻为“模特”的。1942 年,这个短篇获晋察冀边区文联鲁迅文艺第一季的季奖,那正是抗战最残酷最困难的阶段,冀中地区血与火的“五一大扫荡”就发生在这一时期。这也是父亲的作品第一次获奖。作为一名“抗战文艺老战士”,这次获奖对父亲而言,印象很深刻。
1970年4月15日,母亲带着无尽的牵挂离开了她挚爱的亲人。这给历经屈辱劫难的父亲,带来雪上加霜的打击。“昔日戏言身后意,今朝都到眼前来”。在几位好友的帮助下,办完丧事的父亲,独自一人躺在谪居的佟楼新闻里十四排小南屋的铁床上,呆呆地望着低矮的屋顶,望着墙上那带着铁棍儿的小窗,卧蚕眉紧锁。丹凤目含悲。他的嘴倔犟地紧闭着一言不发。往事历历,在脑海中闪现,妻关切的话语又响在耳边…… 就在这张单人铁床上,因白日遭受当众“坐飞机”被揪斗的奇耻大辱,是夜他鼓起勇气愤然触电自杀但被灯口弹了回来。事后他告诉妻,妻哆嗦着嘴唇满眼是泪:“咱不能死,咱还要活着,还看世界呢!”“这人啊,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十年过来看高低!”是母亲的劝说、激励,帮助父亲活了下来。
就在这与两个年轻的疯子为邻的平房小屋,父亲与母亲见面的机会也不多,父亲偶尔回家取几件衣物、吃顿饭,就又得回去接受隔离审查,做那斯文扫地的“卫生”,写那写不出一行半句的“检讨”。交代那交代不出来的“反党”罪行,看那“触及灵魂”的 “革命行动”升级。但他们的两颗心无时无刻不在互相牵挂。只要父亲一进小屋。母亲马上就到对面砖搭的小厨房内,在煤球炉子上做碗挂面汤,端给满面霜侵的父亲。父亲暖暖肚肠对知冷知热的妻小声讲几句触目惊心的所见所闻,为老干部的遭遇愤愤不平:“这是要把国家搞成什么?!”为国家民族的命运深深担忧。别看父亲体质瘦弱,可他是非分明、疾恶如仇,铜枝铁干无媚骨,不管形势多么复杂、多么混乱,他头脑清醒不盲从,更不做违背良心良知的事情。所以母亲常说:“你这个人好拉横车。”意即不大随大流儿。在冰连地结的寒气“包围”中,在随处可见的鄙夷白眼 “扫射”下,患难与共、情德交融的夫妻情,温暖着两颗沧桑多难的心。那时,我大姐、二姐都已在父母的支持下,先后支援外地建设。哥哥因家中狭窄,也只好住在厂里。我和母亲睡在一张稍大的木床上,父亲偶尔回来就睡在靠小窗的铁床上。
父亲心爱的书,连柜子一块儿被抄走了,剩余的几件家具搬来前也贱价处理了。即使这样,屋里还是挤得几乎没有走道儿的地方。吃饭就在铁床上摆张小桌,切菜做饭也全在上面。
小南屋墙薄门陋,屋小炉大,里热外冷,母亲不幸又患了肺炎。我和哥哥用三轮车把她拉到医院央求了半天才住进去。记得父亲请了假,从郊区干校赶去看她。那是个白天,父亲穿得很旧,脸晒黑了,很瘦。脚上一双旧球鞋。看起来更像个农民。病房极大且嘈杂,挤着一圈儿十几个危重病人,父亲没地方坐,就一直贴着床边弯着腰和我母亲说话,宽慰着她。看得出,父亲一直强忍着酸楚,可母亲苍白憔悴的脸上漾起了笑容。
P1-4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