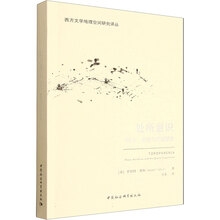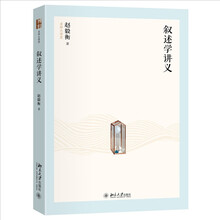《泰戈尔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
一枝“毒”秀批泰翁 《青年杂志》时代的陈独秀是一位启蒙者,之前的陈独秀则是一个带有无政府主义色彩的革命者,上海暗杀团、岳王团、辛亥革命等,他逐一切实参与,但辛亥革命后换汤不换药的现实让他对政治革命感到失望。于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经典转变方式也在其身上应验:欲革命,必先启蒙,才不会再出现“人血馒头”式的悲剧,而启蒙之关键,在于先“救救孩子”,必先从青年人手,于是他才起意创办《青年杂志》,而《青年杂志》(1卷第1号)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敬告青年》,泰戈尔的名字赫然在列。而第二篇文章,则是《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两篇文章纵论古今中西,虽然泰戈尔只是陪衬,甚至是反面典型,但其中包含的一些观点,在后来陈独秀激烈批判泰戈尔时,都发扬光大了。
关于东西方文明问题。陈独秀从生物进化的角度,认为西方文明优于东方文明,中国要进步,就须接受西方文明,摒弃中国传统文化。何为西方文明?《敬告青年》中列举了人权、平等、进化论、科学等。
而在《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中,他则明确提出:“近代文明之特征,最足以变古之道,而使人心社会划然一新者,厥有三事:‘一日人权说,一日生物进化论,一日社会主义,是也。”这与陈独秀所精炼概括的西方文明的精粹即“德先生”与“赛先生”相比,明显混乱。
引进西方思想的第一步当然就是翻译。《新青年》亦因此而颇重视翻译。而文学,在陈独秀看来,则是启发民智,传播启蒙思想的有效工具,因为西方大文豪之大,在他看来,“非独以其文章卓越时流,乃以其思想左右一世也。”鉴于此,《新青年》从创刊之初,就重视对外国文学的介绍和翻译。陈独秀则连续发表介绍西方文学的文章,将左拉、龚古尔兄弟、福楼拜、都德、屠格涅夫、莫泊桑、托尔斯泰、左拉、易卜生、屠格涅夫、王尔德、梅特林克等介绍给国人,同时也身体力行,翻译了泰戈尔的《赞歌》,虽然似乎说明不了他对泰戈尔有多少了解,但他看重泰戈尔的诗名,尤其是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与他的“大文豪”概念也是相通的。除此之外,他还动员胡适、刘半农等翻译西方文学作品,而刘半农之所以成为中国泰戈尔翻译者第二人,则直接受陈独秀影响(他翻译了泰戈尔《新月集》中的两首诗:《恶邮差》和《著作资格》;其“译诗十九首”则包括泰戈尔的《新月集》中的《海滨》五首和《同情》两首)。
相较于对西方文化的热情介绍,从“五四”开始,陈独秀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国粹和东方文化一直持激烈批判态度,视之为国之妖孽,精神鸦片,是阻滞中国现代化的中国封建文化势力的保护伞。在新旧文化问题上,陈独秀从不含糊、从不骑墙,历来旗帜鲜明:那就是身先士卒,冲锋、冲锋、再冲锋! 陈独秀是其中一个最早将泰戈尔介绍到中国的人,也是批判泰戈尔最不遗余力,批判文章写得最多的人。这种前后态度的变化,与陈独秀前后身份不同有关。介绍泰戈尔时,他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反对泰戈尔时,他已成为共产党的主要领导人,政治批判标准代替了文学批评标准。早在泰戈尔来华之前的三月份,陈独秀就拟在《中国青年》上出一期反对泰戈尔的特号,后因故未果。泰戈尔来华之后,陈独秀频繁地在政治性刊物《中国青年》、《向导》上发表一系列批评泰戈尔的文章,对泰戈尔发起连续、猛烈的轰击,犹如再现了当时只手打倒孔家店时的风采。他从反封建、反传统的立场,批评泰戈尔是个极端排斥西方文化、极端崇拜东方文化的人,说他只是“多放莠言乱我恩想界”,只会导致中国社会的落后与挨打;而他抨击科学及物质文明,奢谈精神文化,无异于劝人“何不食肉糜”的昏君,和“牧师们劝工人‘向上帝求心灵的安慰胜过向厂主做物质的争求’同样混帐,象这样颠倒乖乱,简直是个糊涂虫,还配谈什么‘爱”。因而他不客气地对泰戈尔说:“太戈尔!谢谢你罢,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的不得了呵!”陈独秀在这里所说的“老少人妖”,实际上所指的就是东西文化论争中的文化保守派,其主要代表除梁启超外,还有张君劢、章士钊、梁漱溟等。陈独秀对泰戈尔的批评很多可以说是信口开河,具体联系,言辞也越来越激烈,政治色彩昭然若揭,即使在一些本与泰戈尔无关的文章中,也不忘顺手把泰戈尔捎上几句;甚至在泰戈尔早已离开中国的6月,他仍然写了《诗人却不爱谈诗》、《太戈尔与金钱主义》,挖苦泰戈尔虽然自称为诗人,到中国后却始终不谈诗;虽然时时辩白自己反对物质主义,却始终不曾放弃物质的享受。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