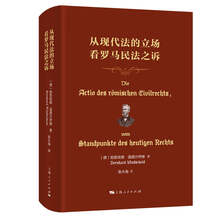《纠纷解决与基层治理》:
再说德行治理。伴随着国家权力的身体退场和技术控制能力的提高,国家权力的通过德行治理的方式日益弱化。这里的德行治理,基于国家权力行使者的思想道德和心理状态对治理效果的影响。在调研中笔者发现,在同样合法的情况下,国家权力行使者运用权力的倾向和心理意愿对于治理的效果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尤其是将当前与20世纪80年代进行对比时,而运用权力的倾向和心理意愿又与其自身的思想道德密切相关。宋庄的村干部也感觉到了这一点,他们说:“乡派出所现在要‘依法行政,,不能像以前一样随便到村里抓人。他们的原则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没有重大伤害,没有出现社会动乱一概不予过问。”“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很多政策都还有约束力,公安部门的权力也比较大,可以随意关人只要你有嫌疑,村民都怕。现在村民法律意识强,公安抓人也要证据,不敢随便关人。”同改革开放之初相比,国家权力行使的策略和倾向确实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改革开放之初,权力的运用适用扩张的心理策略,即无条件维护社会治安,以杜绝社会危害为要点,这一目标在技术条件有限的情况下,高度依赖崇高的思想道德要求;而现在权力的运用则适用自我保护的心理策略,有条件的维护社会治安,同时要考虑自我保护,以不出事为要点。
改革开放之初,维护社会治安是警察的基本目的,是警察实现为人民服务的有效途径,甚至和他们的人生意义联系在一起;而现在则成了一种工作和职业,变得只与职业道德相关,而与意义、精神、思想道德无关。一个村干部讲,有一次他在镇上市场看到两伙人各十五个打群架,两个警察穿着短裤正在一旁围观。他们之所以这样,可能是觉得没有人认识他们,而这个村干部负责治调工作,刚好认识他们。村干部觉得,无论是否穿有制服,是否在工作时间,警察都应该上前制止。应该说,村干部的这种认识恰恰是基于1980年代的德、行结合的思维方式,就是将思想道德和日常工作结合起来的“政法”思维方式,日常工作是思想道德的行动,思想道德是日常工作的指导纲要。显然,这种思维方式已经逐渐被放弃。现在,思想道德和日常工作经历了一个祛魅的过程,两者被严格区分开来,日常工作不再需要的思想道德的武装和指导,国家权力的行使者对自己工作的认同越来越只是一种职业认同。当前,国家权力的运作越来越倚重技术层面,社会秩序越来越依赖于技术治理。技术水平的提高,使得身体治理方式和德行治理方式有条件逐渐退出国家权力治理的日常领域。技术治理确实可以解决很多问题。否则,仅有身体治理和德行治理方式的退出,乡村社会将陷入彻底的混乱。但身体治理和德行治理并不能被技术治理完全替代,前者所能解决的问题并非后者全部能够解决。
国家权力的身体在场可以从某种程度上抑制村庄内依赖小亲族的“拳头风”,抑制村庄内部的恃强凌弱,其关键在于弱者可以轻便求助于在场的国家权力。当国家权力的身体远离村庄的时候,权力技术的提高可以起到替代作用,同样可以有效甚至更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国家意识形态使人们高度认同受法律规制的乡村秩序,通讯和交通的发达使得国家权力可以快速到场。但技术治理的替代作用终究有限,国家权力的身体在场与技术可以快速到场毕竟还是有所不同。一方面,技术治理给潜在的越轨者的心理震慑力并不足够;另一方面,技术治理难以完全有效应对社会流动所带来的新问题。乡村混混所带来的暴力和不平等问题与熟人社会中的暴力关系毕竟不一样,后者主体明确而具体,扎根在本乡本土,“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国家权力在运作中可以通过技术营造快速到场的效果;而前者总处于流动状态,对于乡土社会而言,它是不熟悉的、不固定的,因此国家权力要在运作中达到同样的效果,付出的成本更高。这样,乡村混混运用暴力的机会成本就降到一个较低的水平上。正是看到了这一点,在国家权力身体不断退场时,我们又看到不少地方开展驻村警务,这实际是重新营造了一种国家权力在场的工作方式,与之前的国家权力的身体治理方式原理一样。
另一方面,当抛弃了传统的德行治理方式后,仅仅依赖技术的新治理方式容忍乡村混混的存在,只要他们不导致恶性事件。因为不导致恶性事件就不会危及权力行使者自身,这符合自我保护的心理策略。但不出现恶性事件实际上只是一种的底线的要求,乡村混混的活动中,恶性事件毕竟只是其中的偶然事件,他们的大部分危害乡村秩序的行为则处在法律的边缘,在新的治理方式下被容忍。这就是村民所说的,“现在赖孩子特别多,小偷小摸,敲诈勒索、寻衅滋事,每年都抓,抓抓放放,就是那几个”。这样一来,权力运作的德行治理方式的衰微,似乎意味着更好的秩序不被追求。当然,乡村混混的这种状态,会逐渐改变他们对机会主义行为的预期,从而迟早会生出恶性事件来。一旦这样,再要进行治理,就只有向权力行使者不断加压,这就是不断上演的“严打”。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