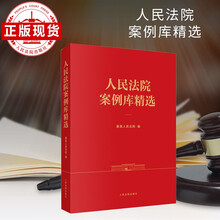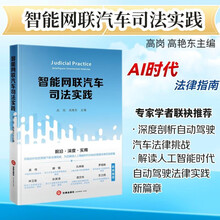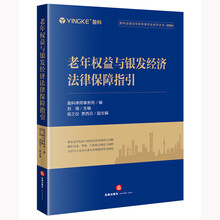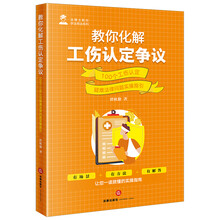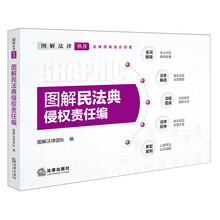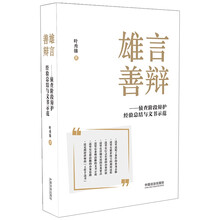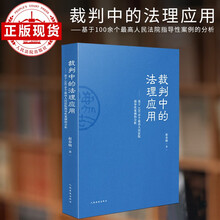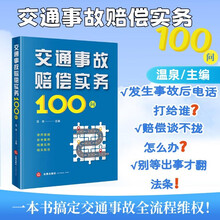所以说终止净额计算的核心要素是三个,一是单一协议,二是提前终止权,三是终止以后的净额计算。刚才提到提前终止权与破产管理人的选择履行权相冲突,其实细想起来,单一协议也是与破产管理人的选择履行权相冲突的,因为我把你的选择前提都取消掉了,在一个合同项下选择哪些义务履行哪些义务不履行,显然是不合适的,所以单一协议也有规避选择履行权的情况。净额计算也与破产法相冲突。之所以抵消要进行审核,就是因为要限制不正常、不应该的抵消,因为抵消就是债务在同等金额内的消灭,消灭债务就是清偿债务。你要净额计算的话,你自己单方决定非破产一方债务清偿了,这相当于你是优先受偿,就与破产法讲的按比例平等受偿的原则直接冲突了。
所以,终止净额计算的核心要素与破产法的规定都是有内在冲突的。而破产法是强制性的法律程序,所以如果没有特别的法律来支持终止净额计算这种机制,那么真正到关键时候它不会起到任何作用。目前,全世界有将近五十个国家,主要是经济发达国家,通过单独的终止净额计算立法或者是修改破产法这种方式为衍生交易的这个机制开了一个口子。在我国新的破产法起草过程中,也对是否在破产法中加入这么一条进行了讨论。当时就提出一个问题,为什么要给衍生市场这么特别的机制?这个问题很经典,原因何在?因为这种机制对于整个金融市场的风险控制,特别是市场系统风险控制具有巨大的价值,就像我们三峡一样具有削峰的价值,衍生交易这种杠杆也是很高的风浪,需要这样的机制削减掉。至于为什么可以,从法律角度说需要做经济分析。我们先回过头分析破产法为什么要规定选择履行,除了债务人和债权人的价值取向以外,还有一个权利是不能给非破产一方的。因为一个企业的资产价值其实不仅仅是每一块资产价值的总和,而是一个持续经营价值,就是整体资产的价值绝对不等于一块块资产价值的总和。如果一个企业是生产某一种特种设备的,需要某一个特定的部件,而这个部件只有一家公司可以提供,那么,这家提供部件的公司若不提供的话,这个破产公司可能什么价值都没有,因为不能生产一个合格的产品。所以,像这种提供各种部件的公司是不能终止合同的,必须继续履行,因为只有你履行合同才能保持这个破产公司的剩余价值。这就是特别履行,因为特别履行比现金履行的价值多得多,必须实际履行。
但是再看金融市场,它是不需要特别履行的,因为金融市场的所有交易不是为了获得产品的使用价值,只是进行价值的管理,都是纯粹的价值。既然是纯粹的价值就不需要特别履行,特别履行毫无意义,也就是说可以随时终止。这就是可以给衍生市场这种特别对待、特别机制的原因,就是因为金融市场的这种特点,这个机制可以说是为衍生市场量身定做的机制。而且为什么要放在破产法里,因为破产法是强制性的法律,要对抗它的强制性原则,必须同样级别才可以,其他部门规章之类根本不管用,所以一定要达到破产法这个级别的立法行动才可以对破产法里面的强制性原则做一些修订。不过很可惜,我们破产法最终没有把这个规定写进去也确实没办法写,就像突然把一个很异类的概念放进去一样,而且感觉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
当然,从长远的发展趋势来看,因为除了发挥这个机制对金融市场的积极作用以外,还是需要进行相关立法的,要通过立法把这个机制限制于需要运用这个机制的情况,规定哪些机构哪些交易可以适用终止净额结算。像美国破产法上,就有很多定量的分析,规定比如一年之内做了多少交易的机构,做了什么类型交易的机构才可以适用这样的机制,而不是说谁都可以用,否则这种机制就没有意义了,市场就会乱套的。我们刚才讲的那些需要特别履行的合同如果也用这样的机制来逃避自己的债务,那经济秩序就会打乱了。而且这样的机制也可能会有一些寻租的现象,通过创设交易,本来不是衍生交易的也设计成衍生交易,利用这样的机制逃避自己的责任的这种情况也会有,这都是需要规范的。而且现在在跨国交易中,国外银行和国内银行做交易的时候通常会提出,我主协议有这样的机制在你们中国法项下能不能承认和执行。甚至在国际上围绕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还有很多做中介服务的机构,比如提供专门对账服务、清算服务的都有。有一些国际机构都开始应用模板了,说合资国家做交易,我信用额度怎么决定,看这几个参数,包括终止净额结算的机制在中国法上承认不承认,承认就是一个参数。金融也是一个很系统、很复杂的工程。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立法,对我国金融机构来说可能至少有一点不利,做交易的时候本来可以做得大一点,但因为没有这样的终止净额计算削减风险,所以只能做小一点,这样就影响交易额了。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