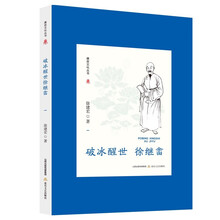光武帝来到严子陵下榻的北军宾社,严子陵知道皇帝御驾亲临,就翻身向里,假装睡熟,不予理睬。光武帝见严子陵如此模样,心中暗笑,随即以故旧老朋友的身份坐到严子陵的床沿上,抚摸着严子陵的背脊,说:“子陵,我今天不是以皇帝的身份,只是以老朋友的身份来看望你,你难道仍不予理睬吗?”严子陵听到刘秀是以老朋友的身份来看望他,当即翻身起来。刘秀又说:“我的老朋友,你难道不肯留在朝中相助于我吗?”严子陵对此未予回答。过了好一会才说:“过去有唐尧这样德行远闻的帝王,也有巢父、许由那样洗耳不从的高士。士各有志,何必相迫呢!”刘秀只好叹息而已。
第二天,光武帝把严子陵请进皇宫,论故道旧,叙谈整日,极为投机。白天讲不完,又作彻夜长谈,向严子陵请教治国良策。谈至深夜,按皇宫规矩,掌灯之后即禁止进出,严子陵只好留宿宫中。光武帝提出两人同榻而眠,边谈边睡。谁知严子陵本性疏狂,睡相不好,竟然将一双脚搁放在光武帝的肚子上。光武帝为了不弄醒严子陵,就任由他搁着。谁知道第二天早朝时,即有太史官禀报,说是“昨夜有客星犯帝座甚急”。言下之意是说皇帝身边有危险人物,要光武帝提防。倒是光武帝宽宏大量,笑着说:“这是我的老朋友严子陵与我同榻共眠,他把脚搁在我身上了。”由此之故,就留下了“客星犯帝座”的佳话,并由此把严子陵当作客星下凡。
我国是一个农业国,农业生产要求人们精勤地观测天象的变化。在上古时代,古人的天文知识是相当普及的。顾炎武曾说:“三代以上,人人皆知天文。”“七月流火,农夫之辞也。”“三星在户,妇人之语也”。“月离于毕,予卒之作也。”“龙辰伏辰,儿童之谣也。”“后世文人学士又问之而茫然不知者矣。”由于历史条件和科学水平,当时的学者不仅以观测天象的变化来确定季节的变换,而且,往往由自然的天象变化联系到人事的因果,“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周易》)。认为天象的变换,“其本在地,而上发于天者也。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
是以明君韧之二宿,伤身正事,思其咎谢,则祸除而福至”。“志日月星辰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凶吉”。尤其到汉代,董仲舒将阴阳、五行、天道结合起来,提出“大一统”学说,以“天人感应论”作为它的理论基础,把天体的运行说成是一种道德意识和目的的体现。他说:“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惕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对策》)认为:“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天地之阴气起,而人之阴气应之而起。人之阴气起,而天地之阴气亦应之而起,其道一也。”(《春秋繁露·同类相召》)按照阴阳五行和天象的变化可以占验吉凶祸福,了解天意。只要观测天象,就能够预决吉凶,把天象、政事、人事牵连在一起。光武帝刘秀即以图起兵,当他登上皇帝位后更是崇信纬,宣布图于天下。自此之后,不仅不轨之徒多假托天象符命惑众谋利,而且举国之内,上下妄谈天命,人人以符命为行动的规范。对“客星犯帝座”,内中同样蕴藏着极深的政治阴谋。
对“客星犯帝座”一事的最早记载,当推东汉时刘珍的《东观汉记》,它记载:“光武与子陵有旧,及登位,望之。陵隐于孤亭山,垂钓为业。时主天文者奏每日出常有客星同流。帝日:“严子陵耳。”访得之,陵不受封。”东晋时史学家余姚人虞预在《会稽典录》中也提到此事:“严遵字子陵,与世祖俱受业长安。建武五年,下诏征遵,设乐阳明殿,命宴会,暮留宿,遵以足荷上。其夜客星犯天子宿。明旦,太史以闻,上日:“此无异也,昨夜与严子陵俱卧耳。”范晔的《后汉书》历来以严谨者著称,他以前人记述汉史事迹的众多史书为依据删繁补缺,成就此史。如事出无因,范晔是不会随意地在短短392字的《严光传》中,浪费笔墨而去专门写上这一传闻之辞的。所以说,“客星犯帝座甚急”必然事出有因。
……
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