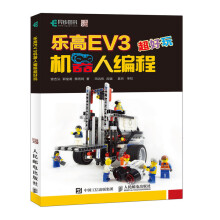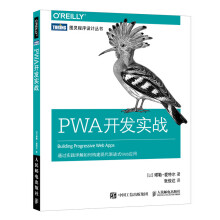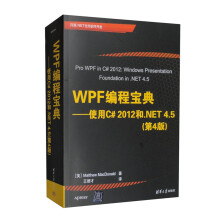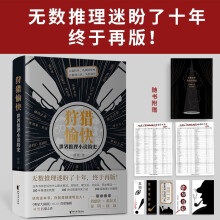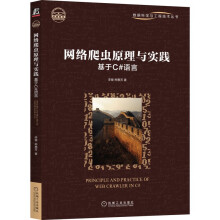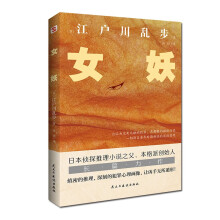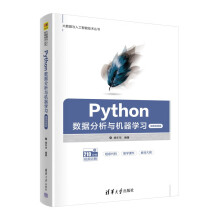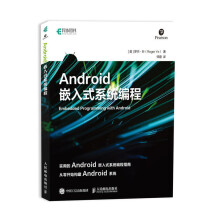随着西方医学的传播和“西医”概念的逐步成型,中国传统医学被逐渐归纳为“中医”。1832年,传教士医生郭雷枢在一份报告中使用了“中医生”的概念。1839年,英、美教会分别在上海开设“中国医院”。1855年美国传教士在武昌、衡阳开设了“中国药房”。1858年陆以括的《冷庐医话》中评述合信的《西医略论》时使用了“西国医士”“中国医人”的概念。此后,常用的有“中国医学,,“国医”“华医”等称谓,到19世纪末,“中医,,逐渐成为与“西医”相对应的概念。②正是由于西方医学的传人,使近代中国医学领域逐渐呈现中医与西医两种不同的医学体系并存的局面。
(一)西学东渐与西医东渐
所谓“西学东渐”,是指从明代晚期以来,西方学术不断向中国传播的历史进程。在17世纪前后,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汤若望、罗雅各、南怀仁等人相继来华,当时这些传教士为了方便在中国传教,积极践行“自我儒化”的路线,同时为了迎合中国士大夫的兴趣,他们将很多天文、历法、地理及数学之类的西方知识带到了中国,如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前六卷及其与李之藻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汤若望的《历法西传》、南怀仁的《欧洲天文学》等。这些知识给当时的中国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影响,但彼时西方尚未开始科技革命,同时传教士本身所掌握的科学知识也相当有限,再加之清乾隆时期开始实施的闭关禁教政策,这一时期西学传播的成果相当有限。
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西学东渐的风潮再次兴起,而不同于其早期的传播,这次西学传播是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而来的,其传播的深度与广度皆远胜以往。在西方列强一次次的军事侵略中,他们的实力展露无遗,西学传播也不断地深化,中国人对于西学的认识从最初的“奇技淫巧”到“中体西用”再到几近于全面的学习与认可。西学的形象也从最初的“夷学”渐次转变为“新学”,与此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和知识体系则成为“旧学”,被戴上了愚昧、落后、迷信的帽子。近代西方数学、物理学、化学、地质学、医学、农学、政治学、经济学、哲学等众多学科体系开始在中国立足并不断发展。①面对着数千年未有的历史变局,近代早期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开眼看世界,开启了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进程。一大批介绍西方科学技术知识的译作也不断问世,目录学家姚明达在《中国目录学史》中说:“自曾国藩创办制造局,以译西书为第一义。数年之间,成者百种。而京师同文馆及西士设教于中国者,先后译录,迄光绪二十二年,可读之书,约三百种。”②西学所带来的冲击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东西方文化在这一时期的碰撞、交融,使整个社会旱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面貌。
P1-3
展开